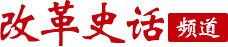知識傳播視域下亞當·斯密的中國觀
發稿時間:2024-02-18 14:55:40 來源:《社會(hui) 科學》 作者:張嘉璈
亞(ya) 當·斯密(1723—1790)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1776年)標誌著現代經濟學的開端。然而,相對不為(wei) 人關(guan) 注的是,斯密在這部具有裏程碑意義(yi) 的作品中曾頻頻提到中國,時不時還有長篇大論,涉及的內(nei) 容主要是清代的經濟和貿易、政治和社會(hui) 等諸多方麵。係統地總結亞(ya) 當·斯密的中國觀,探尋斯密的“中國知識”來源,有助於(yu) 了解斯密本人及當時歐洲的“中國知識”的總體(ti) 水平,並體(ti) 悟相關(guan) 中國敘事對國際認知和理論構建的意義(yi) 。
一、基本論斷:一個(ge) 富有卻停滯的農(nong) 耕國度
雖然《國富論》旨在闡述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但與(yu) 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家相比,亞(ya) 當·斯密仍比較重視經驗事實的歸納,而不是抽象原理的推演,“好幾代經濟問題作者都把《國富論》當作一本可靠的事實性資料書(shu) 而大加引用,乃至今天仍有這方麵的用處”。斯密在大量寫(xie) 到歐洲及美洲殖民地經驗事實的同時,對中國及印度等東(dong) 方國家也有不少細節性論述。大體(ti) 而言,斯密述及中國的基本國情與(yu) 總體(ti) 發展狀況、農(nong) 業(ye) 的成熟與(yu) 工商業(ye) 的欠缺、貧富的懸殊與(yu) 窮人的境況、稅收製度與(yu) 公共設施的特征、外貿的欠發達及增長的趨勢、與(yu) 歐洲的金銀比價(jia) 及購買(mai) 力等。可見,斯密在書(shu) 中對中國的涉及麵相當廣泛。
首先,斯密了解到,多個(ge) 世紀以來,“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且最勤勉的國家”。富裕的表現之一是“中國的米價(jia) 比歐洲各地的小麥價(jia) 格低廉得多”,“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jia) 格,大相懸殊”。斯密進一步聲稱:“在中國廣州地方,半盎司白銀所可支配的勞動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倫(lun) 敦一盎司白銀所可支配的也許還要大。”從(cong) 國際發展層級來看,據斯密觀察,中國和印度、日本等國,“雖然沒有比較豐(feng) 富的金銀礦山,在其他各方麵卻比墨西哥或秘魯更為(wei) 富裕,土地耕種得更好,一切工藝和製造業(ye) 更為(wei) 進步”。有時斯密甚至指出:“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相信中國長期處於(yu) “世界上最富”的狀態,是斯密中國觀的一個(ge) 基本前提。
然而,斯密同時反複強調,中國的發展實已停滯,這種停滯且可能為(wei) 時已久。他寫(xie) 道:“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yu) 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guan) 於(yu) 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yu) 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麽(me) 區別。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不過尚需注意,在斯密的觀念中,停滯並非最糟糕的狀態,隻是意味著缺乏或不再進步,因為(wei) 按其分類,社會(hui) 或國家分為(wei) 進步、停滯、退步三類,中國尚處於(yu) 中間的狀態,可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yu) ”。
據斯密判斷,“中國雖可能處於(yu) 靜止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那裏,沒有被居民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聽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勞動,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未顯著減少。所以,最下級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雖很缺乏,但還能勉強敷衍下去,使其階級保持著原有的人數”。按斯密的描述,當時東(dong) 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幹殖民地,才存在退步現象,表現為(wei) “維持勞動的資金減少”、就業(ye) 競爭(zheng) 異常激烈、勞動工資跌至穀底、底層紛紛淪為(wei) 乞丐或罪犯、上層階級也受到波及、總人口隨之減少。相比之下,18世紀的中國確未滑落到那種衰敗境地。
總之,斯密對中國的基本判斷是:既屬“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又已長期“停滯”,財富積累似已達到極限。這兩(liang) 方麵並不矛盾,斯密是這樣解釋的:所謂“最富”係指一國財富“已達到它的土壤、氣候和相對於(yu) 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因而沒有再進步的可能,盡管尚未退步”,其人口“已完全達到其領土所可維持或其資本所可雇傭(yong) 的限度”;而所謂“停滯”是指,“在這種狀態下,它的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也許都非常的低”,“各種行業(ye) 所適用的資本,就達到各行業(ye) 的性質和範圍所允許使用的程度。這樣,各地方的競爭(zheng) 就大到無可再大,而普通利潤便小到無可再小”。
斯密就是以這種“財富增長已經見頂”的觀念來看待中國的,他進一步強調,“中國似乎長期處於(yu) 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製,那麽(me) 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這裏進而反映了斯密的一個(ge) 重要思想,即一國的政法製度左右著一國財富的程度,決(jue) 定著一國既有要素所能聯合達到的財富限度,要突破限度就必須創造新的製度。無奈,前現代的中國呈現出很強的製度穩定性,無論是“秦製”“大一統”,還是“朝代循環” “超穩定結構” “長期停滯不前”,等等,講的都是這種情況,斯密顯然早已具備這一見識。
問題是,傳(chuan) 統製度或者生產(chan) 技術和組織形態可以保持不變,人口卻是個(ge) 生生不息的變量,尤其是清代在18世紀發生了工業(ye) 革命之前的“人口爆炸”。斯密故而把眼光投到支撐人口的農(nong) 作物上。在斯密看來,中國這樣的“產(chan) 米國”與(yu) 歐洲那些“產(chan) 麥國”相比,“即使麵積相同,產(chan) 米國的糧食,亦必較更為(wei) 豐(feng) 富。這些國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當製度及政策一成不變或缺乏彈性時,在人口基數龐大又增長較快的情況下,一國就很容易步入發展逼近極限並盛極而衰的境地。這一點正是後世學者持續探究的一個(ge) 規律,學者們(men) 談論中國在清代後期出現“內(nei) 卷”和“勤勞革命”而非“工業(ye) 革命”,乃至東(dong) 西方出現了所謂“曆史大分流”,所指即為(wei) 斯密論及的傳(chuan) 統中國那種狀況。
斯密具體(ti) 描述了中國勞動報酬低劣、勞工生活困苦的情況。他指出:“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guan) 於(yu) 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以贍養(yang) 家屬的記述,則眾(zhong) 口一詞。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mai) 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不僅(jin) 如此,斯密還認為(wei) 中國的手工匠人的生存狀況甚至“更為(wei) 惡劣”。他說:“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nei) 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wei) 搜尋或者說為(wei) 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dong) 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
麵對中國這些窮困落後現象,斯密數次明確斷言其根源:“這是因為(wei) 歐洲大部分處在改良進步狀態,而中國似乎處在停滯狀態”; “必須記住,不同國家不同真實勞動報酬的比例,不受各該國實際貧富程度的支配,而受該國進步、退步或停滯等狀態的支配”。借斯密的判斷,不難看出,清代中國或已達到傳(chuan) 統農(nong) 耕社會(hui) 的發展頂點,可惜在西方現代工商文明興(xing) 起的背景下,那終究是王朝的落日餘(yu) 暉。如今我們(men) 在回望世界史時已然看清,18世紀確為(wei) 東(dong) 西方發展的一個(ge) 分叉點,也是中國盛極而衰的曆史轉折點。再讀《國富論》,仍不能不佩服斯密中國觀之先見性。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嚴(yan) 複在譯介《國富論》時會(hui) 寫(xie) 道:“斯密氏,蘇格蘭(lan) 人也,生於(yu) 雍乾之際,而其言乃若為(wei) 今之中國發者。時之相去,百有餘(yu) 年,地之相暌,十餘(yu) 萬(wan) 裏,而燭照籌稽無以過其明如此,此吾所不得不低首而誠服也。悲也!”
二、問題診斷:受限於(yu) 貿易和工業(ye) 的欠發達
透過斯密對中國的描述可以發現,其實他還揭示了造成停滯局麵的另一個(ge) 關(guan) 鍵因素,這就是中國對農(nong) 業(ye) 的偏重和對工商業(ye) 的輕視。雖然有評論者認為(wei) ,“斯密本質上是個(ge) 前工業(ye) 時代的經濟學家,並未倡導把農(nong) 業(ye) 資源轉移給製造業(ye) ”, “他的學說具有顯著的前工業(ye) 化特點”,“從(cong) 未考慮過工業(ye) 生產(chan) 帶來的指數級經濟增長這樣的新因素”,但是斯密依然基於(yu) 東(dong) 西方的比較,看到了中國工商業(ye) 欠發達的問題。他寫(xie) 道:“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nong) 業(ye) 。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you) 於(yu) 農(nong) 業(ye) 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nong) 業(ye) 勞動者的境遇卻優(you) 於(yu) 技工。在中國,每個(ge) 人都很想占有若幹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與(yu) 此同時,“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 ……除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隻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liang) 個(ge) 。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範圍,要是本國船隻或外國船隻能比較自由地經營國外貿易,這種範圍當然就會(hui) 大得多”。
在另外幾處,斯密更明確談到,“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近代中國人跟“極不注意國外貿易”的古埃及人一樣,“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nei) 商業(ye) 而致富的”; “中國的對外通商,向來就不發達”,它一如古埃及和古印度,“也隻主要擅長農(nong) 工業(ye) ”,即簡單的農(nong) 產(chan) 品加工。令斯密感到奇怪的是,中國實際上擁有良好的外貿條件:“中國東(dong) 部各省也有若幹大江大河,分成許許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著,擴大了內(nei) 地航行的範圍。這種航行範圍的廣闊,不但非尼羅河或恒河所可比擬,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塵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國人跟古代埃及人、印度人一樣,“都不獎勵外國貿易,他們(men) 的財富似乎全部得自內(nei) 陸的航行”。
當然,斯密也認識到,中國的對外貿易近期已逐漸活躍起來,中國的出口品,首先是茶葉和瓷器,越來越為(wei) 歐洲人所喜歡。據悉,“十六世紀中葉以前,歐洲用茶,極其有限,不過把它用作藥品。然而現在,英國東(dong) 印度公司為(wei) 本國國民當作飲料而輸入的,每年計達一百五十萬(wan) 鎊。但這還不夠滿足需要,又由荷蘭(lan) 各港和瑞典的哥德堡,不斷秘密輸入。而且,在法國東(dong) 印度公司繁榮時代,又常由法國海岸秘密輸入”。此外,對於(yu) 中國的瓷器等東(dong) 方物產(chan) ,“歐洲的消費額也以幾乎同樣的比例增加”。斯密也注意到,“俄羅斯人,最近也組織所謂商隊,取道西伯利亞(ya) 及韃靼,徑赴北京與(yu) 中國進行正規的交易。總之,除法國東(dong) 方貿易因最近的戰爭(zheng) 而被毀滅了以外,其餘(yu) 各國對東(dong) 方的貿易,幾乎無不在繼續擴大”。
斯密尤其提及,中國及印度的生絲(si) 正在大量輸入英國,乃至英國為(wei) 了自保而設置高關(guan) 稅,而他卻讚成免稅輸入,為(wei) 的是倒逼英國增強自身的絲(si) 絨製造能力。斯密還從(cong) 側(ce) 麵談到,中國當時位居英國在歐洲以外的三大貿易夥(huo) 伴之列,僅(jin) 次於(yu) 北美弗吉尼亞(ya) 和印度。正是因為(wei) 中國日益被拖入世界貿易流,所以會(hui) 出現這種情況:“秘魯的銀,不僅(jin) 在歐洲找到了銷路,而且通過歐洲,也在中國找到了銷路”;“秘魯銀的價(jia) 格,換言之,秘魯銀在當地所能購買(mai) 的勞動量或貨物量,不但對歐洲銀礦上銀的價(jia) 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上銀的價(jia) 格,也有影響”。這與(yu) 當時日本的銅流向歐洲、西班牙的鐵流向智利和秘魯等等相同,反映了新興(xing) 的全球化貿易態勢,而中國顯然已開始卷入這種全球化貿易流。
然而,即便如此,斯密仍強調,中國對外貿易總體(ti) 上“並不繁盛”,而且其“剩餘(yu) 生產(chan) 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國人運到外國去,換回它們(men) 所需要的其他東(dong) 西,那常常是金銀”。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出口,“有大部分為(wei) 外國人經營”,而且主要不是為(wei) 了直接的生產(chan) 和消費。雖然斯密認為(wei) ,外貿經營無論掌握於(yu) 外國還是本國資本手中本身“無關(guan) 重要”, “縱使本國輸出業(ye) ,有大部分為(wei) 外國人經營,這國國民的富裕,仍可達到極高的程度”,可是,對外運輸業(ye) 為(wei) 外國人所主導,這畢竟反映了中國對外貿缺乏熱情甚至本能拒斥的心理。斯密為(wei) 此而舉(ju) 例:“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當俄國公使蘭(lan) 傑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慣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men) 乞食般的貿易!’”這樣的態度在斯密身後繼續再現。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率團來華尋求擴大貿易時,乾隆皇帝照例擺出了一副高高在上、抵製外貿的姿態。
問題的嚴(yan) 重性在於(yu) ,文明的發展需要彼此交往,貿易活動本身又與(yu) 工業(ye) 進步密切關(guan) 聯。斯密依據歐洲的經驗而斷言,“製造業(ye) 常常需要國外貿易來支持”。他承認,在中國東(dong) 部的幾個(ge) 省,盡管“似乎也在極早的時候就已有農(nong) 業(ye) 和製造業(ye) 上的改良”,也盡管被“推為(wei) 世界上最富”,但是,那實際上僅(jin) 限於(yu) 農(nong) 產(chan) 品簡單加工及農(nong) 村小手工業(ye) 。外貿交易的欠缺意味著外部激勵的缺失,終究影響到了工業(ye) 或製造業(ye) 的不斷進步。更有甚者,斯密深知,傳(chuan) 統中國的大政方針始終“比較有利於(yu) 農(nong) 業(ye) ,比較不利於(yu) 製造業(ye) 及國外貿易”,這一點迥然有別於(yu) 重視工商業(ye) 或“城市產(chan) 業(ye) ”的“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
令斯密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幅員那麽(me) 廣大,居民是那麽(me) 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chan) 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ge) 廣大國內(nei) 市場,就能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ye) ,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麵積而言,中國的國內(nei) 市場,也許並不小於(yu) 全歐洲各國的市場”。他斷言:“假設能在國內(nei) 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yu) 各地的國外市場,那麽(me) 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強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ye) 的生產(chan) 力。如果這種國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則尤有這種結果。”斯密甚至想得更遠:“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hui) 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yu) 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chan) 業(ye) 上其他各種改良。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men) 除了模仿他們(men) 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hui) 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men) 自己。”
到斯密時代,英國的工業(ye) 革命已在發動,商業(ye) 革命則在歐洲範圍內(nei) 早已發生,因此,中國重農(nong) 輕商、工業(ye) 缺乏而致發展停滯日益成為(wei) 一個(ge) 搶眼的可悲事實。由此帶來的後果是,恰如斯密注意到的,中國君主的歲入,一如古埃及和印度曆來的君主,“幾乎都是以土地稅或地租為(wei) 唯一源泉。租稅征收額的大小,取決(jue) 於(yu) 土地年產(chan) 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與(yu) 收入,與(yu) 國境內(nei) 土地的墾治狀況,以及土地產(chan) 物數量的多寡,土地產(chan) 物價(jia) 值的大小,必然有極大的直接關(guan) 係”。一方麵,因為(wei) 農(nong) 業(ye) 經營績效相對於(yu) 工商業(ye) 更不穩定,會(hui) 因為(wei) 農(nong) 業(ye) 收成豐(feng) 歉的不同而致“租稅也一年不同於(yu) 一年”;另一方麵也會(hui) 進一步強化重農(nong) 傾(qing) 向,造成“國家的君王,當然特別注意農(nong) 業(ye) 的利益,因為(wei) 他們(men) 年收入的增減,直接取決(jue) 於(yu) 農(nong) 業(ye) 的盛衰”。
不過,在斯密看來,重農(nong) 社會(hui) 縱有千短也有所長,這是因為(wei) ,君主歲入在一個(ge)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與(yu) 土地的產(chan) 出量直接相關(guan) ,所以,為(wei) 了“要盡可能使這種生產(chan) 物又豐(feng) 盈又有價(jia) 值,勢須使它獲有盡可能廣泛的市場。要做到這樣,必須使國內(nei) 各地方的交通既極自由,又極方便、極便宜。而維持這種交通狀態,惟有興(xing) 築最好的通航水道與(yu) 最好的道路”。按斯密推斷,這就是中國水運等公共工程得以維護較好的原因所在。他談到,“據說中國的君主、回教治下的孟加拉君主、古代埃及君主為(wei) 求盡量增加其國內(nei) 一切土地生產(chan) 物的分量和價(jia) 值,都曾竭盡心力,從(cong) 事公路及運河的創建與(yu) 維持,使得每一部分生產(chan) 物,都能暢銷於(yu) 國內(nei) ”。斯密表示,這一點與(yu) 歐洲公共交通設施的“慘淡經營”和“漫不經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上述看法的合理性尚可商榷,其實,大國都必然需要更好地維護交通和水利之類設施,有的學者甚至認為(wei) ,中華帝製本質上起源於(yu) 並仰賴於(yu) 治水工程。斯密也述及中國的交通,稱“在中國,在亞(ya) 洲其他若幹國家,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這兩(liang) 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據說,朝廷頒給各省疆吏的訓示,總不斷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這一部分訓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決(jue) 定其黜陟進退的一大標準。所以,在這一切國家中,對於(yu) 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別在中國是如此。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隻不過,正如後世學者所言,由良好基礎設施所支撐的大一統王朝,卻往往是“典型的發展死胡同”,因為(wei) 維持穩定現狀與(yu) 尋求不斷發展遵循的是兩(liang) 套邏輯,斯密的中國觀是否已經蘊含了這一思想呢?
三、縱觀曆史:探索斯密“中國知識”的來源
綜觀以上論述可知,斯密有關(guan) 中國的論述在總體(ti) 上基本符合實情,是有先見性的。他的一些關(guan) 鍵論斷,無論是認為(wei) 中國達到了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財富“天花板”,這個(ge) “天花板”本質上由法律和製度設定,由此導致經濟發展長期陷入停滯;還是斷定傳(chuan) 統中國的問題症結在於(yu) 重農(nong) 抑商、閉關(guan) 自守、工業(ye) 和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和航運得不到發展,以及人口過剩狀態下民眾(zhong) 勤勞而貧窮,等等,無疑都抓住了中國經濟、政治、社會(hui) 諸方麵的核心特征。正因如此,除了前引嚴(yan) 複的欽佩之辭外,國內(nei) 當代學者也認為(wei) ,雖然“斯密對當時中國的實況所知甚少,但他的評論總的精神是完全中肯的”。不過,這個(ge) 看法中也有尚欠精確的地方,因為(wei) 很難想象,斯密對中國評論的“完全中肯”能夠建立在對中國“所知甚少”的基礎上。
及至斯密生活的18世紀,歐洲實已積累了頗為(wei) 豐(feng) 富的有關(guan) 中國的知識。且不說13世紀馬可波羅的遊記所通報的中國情況,至少繼葡萄牙人1557年在澳門建立貿易據點後,東(dong) 西方之間的交流日益穩定地擴大開來,歐洲的對華了解自然不斷直接、具體(ti) 、明確起來,哪怕有關(guan) 知識“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chuan) 教士”。然而,如果說那些偶然的遠行者和逐利的生意人是在非正式地傳(chuan) 播“中國知識”,則另外也有越來越多的精英階層在正式地把“中國知識”傳(chuan) 回歐洲。“1600年後,通過耶穌會(hui) 士的信劄,有關(guan) 中國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後,關(guan) 於(yu) 中國的書(shu) 籍開始廣為(wei) 人知。這些書(shu) 用多種歐洲語言出版,不僅(jin) 從(cong) 總體(ti) 上介紹了中國的許多卓越成就,還更具體(ti) 地介紹了中國的技術和經濟思想”,總之,這是一個(ge) “中國知識”開始大爆發的時期,因為(wei) “17世紀期間,出現了數百本由傳(chuan) 教士、商人、醫生、稅收、士兵及自由旅行家寫(xie) 的關(guan) 於(yu) 亞(ya) 洲的書(shu) 籍”,其中“有60本左右是寫(xie) 東(dong) 亞(ya) 的”。
歐洲的“中國熱”以及隨後歐洲知識圈對中國的仰慕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1700年被視為(wei) 歐洲“開始鍾情於(yu) 中國的轉折之年,因為(wei) 隨後80年裏,許多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產(chan) 生如此強烈的好奇”,“許多啟蒙思想家積極地與(yu) 中國和中國的思想聯係在一起”。經濟學界自然也不例外。重農(nong) 學派經濟學特別是學派著作中所反映的中國印記,尤其是學派領袖弗朗斯瓦·魁奈1767年發表了《中華帝國的專(zhuan) 製製度》,學派重要人物杜爾哥“專(zhuan) 門為(wei) 兩(liang) 位中國留法青年撰寫(xie) 中國問題集及其序論”即發表於(yu) 1766年的《關(guan) 於(yu) 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均表明18世紀中葉歐洲對中國的知識水平已達到了不可小覷的程度。沒有這樣的歐洲對華知識背景,是無法形成斯密那個(ge) 較為(wei) 全麵的中國觀的。這一點也為(wei) 英國學者所承認,因為(wei) 他們(men) 看到,“斯密背後是法國的重農(nong) 主義(yi) 者魁奈,而關(guan) 鍵的是,在魁奈的背後是中國”。
斯密從(cong) 1764年起陪伴巴克勒公爵遊學法國,“在國外逗留了兩(liang) 年半”,其中“在巴黎待了十個(ge) 月”, “經常在這裏會(hui) 見杜爾哥”,“同杜爾哥到處會(hui) 麵”,交談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甚至在斯密回國後仍與(yu) 杜爾哥有書(shu) 信交流,難怪“杜爾哥的論證對斯密的思想所發生的影響,任何讀過《關(guan) 於(yu) 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和《國富論》的讀者都很容易看到”。1766年歸國前,斯密也多次見過魁奈,他非常推崇魁奈及其思想,相信魁奈創立的重農(nong) 學派“最接近於(yu) 真理”,以至曾想把《國富論》獻給這位(斯密眼中)“居於(yu) 全世界首位的經濟研究工作者”。此外,就在魁奈那裏,斯密聽到重農(nong) 學派人士談及法國財盡國窮時說,“如果不去征服中國那樣的國家……這個(ge) 國家就不可能獲得新生”。總之,重農(nong) 學派關(guan) 於(yu) 中國富裕的總體(ti) 觀念,尤其是有關(guan) 自由貿易、自然秩序、以簡馭繁、無為(wei) 而治之類理念,一般認為(wei) 都影響過斯密,而這些思想都有顯著的中國淵源。
斯密本次海外旅行期間,在日內(nei) 瓦的兩(liang) 個(ge) 月中也“見過伏爾泰五六次”,眾(zhong) 所周知,伏爾泰相當了解中國情況並且高度讚美中華文明,他可是“斯密最崇敬的在世的偉(wei) 人”,彼此有過範圍甚廣的交談;斯密曾稱頌“伏爾泰的書(shu) 是為(wei) 一切人寫(xie) 的,一切人都在讀”,這自然包括伏爾泰讚美過中國的《哲學詞典》等書(shu) 。因此,以斯密在法國的廣泛交遊、其時法國知識界對中國的高度推崇、蘇格蘭(lan) 跟法國曆來的密切聯係、斯密基本的法文閱讀能力,以及斯密從(cong) 法國“返回英國時帶回了至少四箱書(shu) ” ——且據推斷,“托運的書(shu) 一定很多”,因為(wei) 僅(jin) 僅(jin) 為(wei) 了從(cong) 倫(lun) 敦運回家鄉(xiang) ,斯密就支付了堪稱巨款的“二百英鎊的保險金”,則斯密的“中國知識”具有較深的法國淵源不再令人驚奇。有一位經濟思想史專(zhuan) 家即指出:“斯密要說的很多內(nei) 容之前已有人說過,隻不過是用法文說的。”確有證據表明,《國富論》的寫(xie) 作正始於(yu) 斯密在法國逗留時期,“此書(shu) 在那時已粗具規模,作者也已讓他的巴黎朋友知道他在進行寫(xie) 作,並就他正在闡述的理論結構中的一些明確論點同他們(men) 進行了討論”。 《國富論》較多篇幅的中國論述實際上折射了當時中國話題在法國的熱門性,並且也是這種時髦風氣的一部分。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分別初版於(yu) 1759年和1776年,其海外(主要是法國)旅行正好發生在二者成稿之間。比較這兩(liang) 部著作可見,《道德情操論》甚少提及中國,一共不過三五次且都十分簡略,這與(yu) 《國富論》提及中國達幾十次且有長篇大論適成對照。盡管這或許與(yu) 論述的主題差異有關(guan) ,但在外遊曆期間受到歐洲大陸“中國知識”傳(chuan) 播的影響肯定是一個(ge) 最值得考慮的因素。當然,這不是要低估英國當時的“中國知識”水平,事實上,作為(wei) 對華傳(chuan) 教、商貿、外交的歐洲先行者,英國到17、18世紀已在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shu) 館和倫(lun) 敦的大英博物館藏有中文書(shu) 籍。其中的牛津大學就是斯密於(yu) 1740—1746年求學的母校,他所在的巴利澳爾學院“擁有一座在牛津大學數得上的最好的圖書(shu) 館”,那整整六年中,“他廣泛而深入地閱讀了許多學科和許多種語言的大量書(shu) 籍,沒有讓時間白白浪費掉”,乃至“損耗了自己的健康”。這麽(me) 看,在當時歐洲社會(hui) 對中國充滿幻想和好感之際,斯密在牛津大學接觸有關(guan) 中國的知識自屬合理之舉(ju) 。當然,斯密此時的“中國知識”與(yu) 其後來遊曆法國所獲得的“中國知識”不可同日而語。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有關(guan) 中國的論述僅(jin) 限於(yu) 中國是個(ge) “偉(wei) 大帝國”、擁有“億(yi) 萬(wan) 同胞”、那裏以“腳大到適於(yu) 行走”的女士為(wei) “醜(chou) 八怪”、“偉(wei) 大的國王萬(wan) 壽無疆”是一種“東(dong) 方式的奉承”、伏爾泰寫(xie) 過“動人的悲劇《中國孤兒(er) 》 ”。而在《國富論》中,斯密在對華認知方麵已展現出準專(zhuan) 家級水平。具體(ti) 考證斯密《國富論》中的中國敘事,大體(ti) 上來自多種渠道,有比較可靠的,也有不甚可靠的。例如,就前述俄國公使請求通商卻遭到北京官吏鄙視的事例,斯密作了一個(ge) 注釋:“參看《北爾遊記》中的蘭(lan) 傑日記,第2卷第258、276、293等頁。”除了這種來源可考且注明出處的地方之外,其他更多的則是籠統言之,如他說有關(guan) 中國水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chuan) 教士”。這句話既顯示了相關(guan) 知識來源,更顯示了斯密的存疑態度。類似存疑的例子還如:關(guan) 於(yu) 浚河修路中的行政效率,“據我所知,至少含有若幹疑問”; “除非我們(men) 認為(wei) 關(guan) 於(yu) 中國……的富裕和農(nong) 業(ye) 情況的那些奇異記載是可以置信的”; “各旅行家的報告……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
事實上,即使斯密參考了當時關(guan) 於(yu) 中國的多種一手記載,那些記載者也不都是訓練有素的記錄者。針對中國公共工程的記載,斯密就明確說過,“假使這些工程,是經過比較有識者的考察,假使這些報道,是比較忠實的目擊者的敘述”雲(yun) 雲(yun) 。這反映出斯密在利用材料上持慎重態度,所以在其文字表述上,可以看到涉及中國的事實與(yu) 觀點中往往帶有“似乎”“也許”“可能”“據說”“有人說”“歐洲有權威的曆史家尚未能予以確證”之類字樣。這種小心謹慎、留有分寸的處理方法自然也充分表明,斯密的“中國知識”存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他自己對此心知肚明,也並不諱言。除了與(yu) 斯密謹小慎微的性格特點和行文風格有關(guan) 外,本質上這也反映了一個(ge) 基本事實,即斯密生活的18世紀終究是一個(ge) 由前現代向現代轉型的時期,那個(ge) 時期歐洲對中國的知識不免處在或明或暗、真假混雜、既有文本依據又不乏道聽途說的過渡狀態,斯密不可能不受此影響。當然,也須承認,即使按照18世紀的學術標準,斯密對征引內(nei) 容的注釋也是不充分的,他“看來借用甚多卻未能標明”,這為(wei) 後人追溯斯密的知識來源平添了難度。
四、放寬視野:理解斯密“中國知識”的意義(yi)
準確可靠的域外知識固然可取,但從(cong) 知識傳(chuan) 播的角度看,縱然是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是多有錯漏的知識,也未必就不能發揮正麵的功能。不甚全麵、不很確切的“中國知識”照樣為(wei) 斯密的經濟理論構建起到了一定的支撐性貢獻。大而言之,前述斯密講到國家或社會(hui) 的三種狀態(即進步、停滯、退步)時,還有講到歐洲重視工商業(ye) 、非歐洲國家隻重視農(nong) 業(ye) 時,中國都是一個(ge) 不可多得的典型,中國的情況有助於(yu) 斯密完善自己的論證、支持自己的結論。中國在很多方麵都成了歐洲現成的比較對象,可對歐洲的發展給予啟示或警示。比如斯密說,“如果不幸,國家專(zhuan) 製,君主暴虐,人民財產(chan) 隨時有侵害的危險,那麽(me) ,人民往往把資財的大部分藏匿起來。這樣,當他們(men) 所時時刻刻提防的災難一旦臨(lin) 頭的時候,他們(men) 就可隨時把它帶往安全地方”;再有,“據說,中國和印度農(nong) 村勞動者的地位與(yu) 工資,都比大多數技工和製造工人高。假如沒有同業(ye) 組合法規及組合精神加以幹預,歐洲各地也許都和中國、印度一樣”。他拿中國作對照,顯然是要歐洲人或英國人引以為(wei) 戒。
其實,在信息傳(chuan) 播手段不夠發達的年代,人們(men) 慣於(yu) 利用某個(ge) 域外國度來表達自己的理想或訴求。例如,伏爾泰、魁奈等人曾高調地讚美中國,而孟德斯鳩、黑格爾等人又嚴(yan) 厲地評判中國,中國形象從(cong) “理性原則”“人文智慧”的典範一變而為(wei) “專(zhuan) 製國家”“墮落民族”,這中間除了歐洲的進步外,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大家都在拿中國說事,要利用異國敘事來解決(jue) 自身的問題。由此觀之,“中國知識”的準確性有時不是最要緊的,關(guan) 鍵是借中國這個(ge) 遙遠、神秘、迥異的國度來增強自己的說服力。故此,我們(men) 甚至可以看到斯密幹脆用中國來進行假設。他說過:“讓我們(men) 假定,中國這個(ge) 偉(wei) 大帝國連同她的全部億(yi) 萬(wan) 居民突然被一場地震吞沒,並且讓我們(men) 來考慮,一個(ge) 同中國沒有任何關(guan) 係的富有人性的歐洲人在獲悉中國發生這個(ge) 可怕的災難時會(hui) 受到什麽(me) 影響。”在這裏,斯密純粹用中國作假想,來探討眾(zhong) 人對遙遠危機的情感反應。可見,具體(ti) 事實的準確性並不重要,就如托馬斯·莫爾幹脆用純粹的“烏(wu) 托邦”來寄托本人的社會(hui) 理想。
進言之,越是在前現代,非正式的異族知識傳(chuan) 播越是發揮著主渠道的作用。然而,哪怕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在數碼技術讓人類即時共享準確知識的今天,口口相傳(chuan) 的非正式知識傳(chuan) 播,甚至有意無意的以訛傳(chuan) 訛也仍在塑造著人們(men) 的思想和行為(wei) ,說到底這是人性使然。世界曆史上更時常會(hui) 發生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即對異族知識的扭曲、對他國信息的誤傳(chuan) ,卻經常起到歪打正著、出人意料的正麵作用。這方麵的例子數不勝數,最突出者莫過於(yu) 哥倫(lun) 布發現新大陸。葡萄牙人基於(yu) 對環球地理的了解,拒不支持哥倫(lun) 布的遠洋探險提議;西班牙人恰恰因為(wei) 相對缺乏環球地理知識,反而資助了哥倫(lun) 布的事業(ye) 。同樣,哥倫(lun) 布至死都堅信自己發現了東(dong) 方的印度,如此卻激發了對東(dong) 方財富的熱望和更多的環球遠航。因此,知識傳(chuan) 播未必總是遵循正確的方法和科學的規律,主觀的東(dong) 西實在太多,機會(hui) 主義(yi) 的隨機應變更是隨處可見,其結果也未必一定是負麵的。故此,在回顧斯密的中國觀時,重要的不是去考證斯密中國論述的準確性(盡管這也不是一點不重要),而是要看到其中國論述對其論證說理的支持作用。事實上,有一派學者相信,斯密“在援用曆史事實和事實材料時受限於(yu) 其構建重大思想體(ti) 係的願望”,換言之,即便他“沒有扭曲事實”,也難免有某種“削足適履”乃至“猜想曆史”之嫌,他對本國《濟貧法》和殖民貿易的論述就“跡近不實的宣傳(chuan) ”,此外其引證也粗糙隨意。
如此看來,對於(yu) 遙遠域外如中國,即使斯密論述中出現某些矛盾,例如涉及對中歐白銀比價(jia) 反映的或貧或富的解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何況斯密的理論本身就多有矛盾之處。如今在經過現代和後現代理論的洗禮後,我們(men) 應該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縱然是確鑿的知識,也未必就擁有全麵的代表性和宏觀的客觀性,因為(wei) 事實的呈現從(cong) 來都蘊含著一個(ge) 選擇性問題。比如,人們(men) 完全可以爭(zheng) 辯,斯密關(guan) 於(yu) 中國的輕徭薄賦,稱“中國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國一切土地生產(chan) 物的十分之一構成,而這所謂十分之一,在許多地方據說還沒有超過普通生產(chan) 物的三十分之一”,即便都是事實,也必然需要關(guan) 注它們(men) 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甚至是否屬於(yu) 某種“孤證” ——這也是學界對斯密曆史事實援用的一種批評。凡此種種都提醒今人,應該用知識傳(chuan) 播的宏大視野來解讀斯密乃至近現代域外諸多人等的中國觀,這樣的視野能使我們(men) 更加抽象而非具體(ti) 、更加通透而非拘泥地理解西方文獻中的中國敘事,如此方能以開放的頭腦從(cong) 中獲得更多更好的啟發。
人類文明的進步,曆來都離不開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學習(xi) 和效仿。人類學家弗朗茨·博阿斯總結道,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能達到怎樣高級的文明狀態,本質上取決(jue) 於(yu) 它跟其他優(you) 秀民族接觸的程度,越是與(yu) 高級文明、先進國家交往得多,就越能跟著邁向更高層次的文明。以此視之,獲取域外知識誠乃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國家加速進步的必由之路,尤其是跨入近代以來,世人更加強烈地生發出對域外他族、遙遠國度的好奇和想象。反過來,域外對我族的敘事論述和形象構建也總是能成為(wei) 他山之石而為(wei) 我所用。正如斯密研究者已提出的那樣,《國富論》在述說中國時傳(chuan) 達的有關(guan) 加強分工、擴大貿易、發展工業(ye) 、打破閉關(guan) 自守、完善法律製度等等思想至今仍屬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良策。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確有必要回首再看亞(ya) 當·斯密的中國觀,經典從(cong) 來都是常讀常新的。
作者是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博士生
友情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