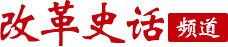亞當·斯密誕辰 300 周年:窮人改善境況的唯一希望是市場經濟
發稿時間:2023-06-14 15:32:40 來源:辛莊課堂 作者: 雷納·齊特爾曼
我們(men) 對亞(ya) 當·斯密這個(ge) 人知之甚少。我們(men) 甚至不知道這位著名的蘇格蘭(lan) 人的生日。我們(men) 所知道的隻是他受洗的日期:1723年6月5日(儒略曆);這意味著,根據我們(men) 的公曆,他在6月16日受洗。他從(cong) 不知道他的父親(qin) ,一位海關(guan) 官員,死於(yu) 44歲,就在亞(ya) 當·斯密出生前幾個(ge) 月。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的母親(qin) ,她不僅(jin) 撫養(yang) 他長大,而且在1784年她去世前一直和他一起生活。斯密終生未婚。我們(men) 隻知道他談過兩(liang) 次戀愛,但他的感情並沒有得到回報,這可能是因為(wei) 他被認為(wei) 長得不太好看。
17歲那年,他開始在牛津大學學習(xi) 六年,但對這所大學並沒有留下深刻印象。他後來輕蔑地談到他的教授,認為(wei) 他們(men) 很懶惰。三十歲之前,他被任命為(wei) 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並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論》。他一生隻出版了兩(liang) 部主要著作,最著名的是 1776 年出版的《國富論》。他寫(xie) 的書(shu) 更多,但生前手稿被燒掉了,所以我們(men) 隻有這兩(liang) 本書(shu) 和他的一些論文和講課記錄。
在那些從(cong) 未讀過斯密的書(shu) 的人中,他有時被視為(wei) 極端自私的支持者,甚至可能被視為(wei) 戈登·蓋科式極端資本家的精神之父,在電影《華爾街》中高呼“貪婪是好的!”。然而,這是一個(ge) 扭曲的形象,源於(yu) 斯密在其《國富論》一書(shu) 中極力強調經濟主體(ti) 的私利。但這樣的畫像絕對是誤傳(chuan) 。
移情作為(wei) 一個(ge) 基本概念
《道德情操論》一書(shu) 的第一章以“同情”一節開頭,亞(ya) 當·斯密在其中將同情定義(yi) 為(wei) “對任何激情都有同感”。今天我們(men) 可能會(hui) 使用“同理心”這個(ge) 詞。斯密說:
“無論人們(men) 會(hui) 認為(wei) 某人是多麽(me) 自私,在這個(ge) 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guan) 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xing) 外,一無所獲。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men) 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chan) 生的感情。”
斯密特別同情窮人。斯密從(cong) 各種來源中獲得收入,每年加起來高達900英鎊,是大學教授工資的三到四倍。但當亞(ya) 當·斯密的遺囑被宣讀時,他的外甥大衛·道格拉斯感到非常失望,收到的遠低於(yu) 他的預期。遺囑證實了斯密的朋友們(men) 長期以來的猜測:斯密幾乎將他的全部財產(chan) 捐贈給了窮人,而且大部分是秘密捐贈的。事實上,他的慷慨甚至導致斯密自己一度陷入金錢困境。
如果你讀過他的兩(liang) 部主要著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你將很難找到他正麵談論富人和權勢的話。在他的書(shu) 中,商人和地主幾乎完全被描繪成負麵的,他們(men) 主要是想維護自己的私利並努力創造壟斷的人:
“我們(men) 的商人和大製造商抱怨高工資在提高價(jia) 格方麵的不良影響,從(cong) 而減少了他們(men) 的商品在國內(nei) 外的銷售。他們(men) 隻字不提高利潤的壞影響。他們(men) 對自己的收益的有害影響保持沉默。他們(men) 隻會(hui) 抱怨其他人。”
“同行業(ye) 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是為(wei) 了取樂(le) 和消遣,但談話最終以反對公眾(zhong) 的陰謀結束,或者以某種提高價(jia) 格的詭計告終。”
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中對資本家的正麵評價(jia) 比亞(ya) 當·斯密著作中任何地方都多。“資產(chan) 階級不斷創造出比過去所有世代的總和還要強大的生產(chan) 力。”馬克思和恩格斯欽佩地寫(xie) 道。斯密的作品中沒有這種欽佩的痕跡。相反,富人是尖刻批評的目標。斯密的捍衛者認為(wei) ,這並不反映對企業(ye) 家或富人的任何普遍不滿,而是斯密提倡自由競爭(zheng) 和反對壟斷。這當然是一方麵,但是,閱讀他的兩(liang) 部主要著作,人們(men) 仍然會(hui) 覺得,歸根結底,斯密不喜歡富人就像他不喜歡政客一樣。甚至亞(ya) 當·斯密也未能擺脫知識分子傳(chuan) 統上對富人懷有的怨恨。
對窮人命運的同情
然而,相反地,斯密有許多段落表現出對“窮人”狀況的同情。他並沒有將自己局限在最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窮人,他也關(guan) 注“不富有的人”,“即, 絕大多數人的狀況,他們(men) 必須用勞動換取工資才能謀生。” 在《亞(ya) 當·斯密的美國》一書(shu) 中,Glory M. Liu 回顧了人們(men) 對亞(ya) 當·斯密的接受和研究現狀:“幾乎一致認為(wei) ,對斯密來說,商業(ye) 社會(hui) 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改善了窮人的狀況。”
《國富論》中有一句名言:“沒有哪個(ge) 社會(hui) 一定是繁榮幸福的,社會(hui) 成員中的絕大部分是貧窮和悲慘的。此外,為(wei) 全體(ti) 人民提供食物、衣服和住宿的人,應該分享他們(men) 自己大量勞動的產(chan) 品,使他們(men) 自己的食物、衣服和住宿都過得很好,這是公平的 。”
今天,這些話有時會(hui) 被誤解為(wei) 斯密提倡政府主導的財富再分配。那不是他的意圖,他當然不是在呼籲社會(hui) 革命。但根據斯密的說法,貧困並不是注定的。不過,最重要的是,他不信任政府。在《國富論》第8章連同上麵引用的句子,他指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徑是通過經濟增長。持續的經濟增長是提高工資的唯一途徑,經濟停滯導致工資下降。在另外的地方,他寫(xie) 道:“饑荒從(cong) 來都不是由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而是政府試圖通過不正當手段來彌補饑荒帶來的不便的暴力行為(wei) 。”250 年後,在數百次(如果不是數千次)嚐試通過價(jia) 格控製來控製通貨膨脹的失敗嚐試之後,我們(men) 完全清楚他是多麽(me) 正確。
斯密寫(xie) 道,“勞動的自由報酬”是“財富增加的結果”,並一再強調“當社會(hui) 朝著進一步獲得……前進時,勞動窮人的狀況,以及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狀況,似乎是最幸福最愜意的。靜中苦,衰中苦。”
另一方麵,卡爾·馬克思認為(wei) 他已經發現了各種必然導致資本主義(yi) 垮台的經濟“規律”,例如“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或無產(chan) 階級的貧困化。在他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中,馬克思表述如下:“隨著資本大亨的數量不斷減少,他們(men) 篡奪和壟斷了這一轉變過程的所有優(you) 勢,苦難、壓迫、奴役、墮落和剝削的現象越來越多;但工人階級的反抗也隨之增長,這個(ge) 階級的人數總是在增加,並且受到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過程本身機製的約束、團結和組織。資本的壟斷成為(wei) 生產(chan) 方式的束縛,而生產(chan) 方式是在資本壟斷的影響下產(chan) 生和繁榮的。生產(chan) 資料的集中化和勞動的社會(hui) 化最終達到了與(yu) 資本主義(yi) 外衣不相容的地步。這外殼被炸裂了。資本主義(yi) 私有製的喪(sang) 鍾敲響了。……但是,由於(yu) 自然法則的無情性,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產(chan) 生了它自己的否定。”
1776 年《國富論》出版時,資本主義(yi) 仍處於(yu) 起步階段,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赤貧之中。貧困在當時的含義(yi) 與(yu) 今天截然不同。人們(men) 瘦弱且骨骼較小——縱觀曆史,人體(ti) 已經適應了熱量攝入不足。安格斯·迪頓 (Angus Deaton) 在他的《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 一書(shu) 中寫(xie) 道:“18世紀的小工人,實際上陷入了營養(yang) 陷阱;他們(men) 不能掙很多錢,因為(wei) 他們(men) 身體(ti) 虛弱,他們(men) 吃不飽,因為(wei) 沒有工作,他們(men) 沒有錢買(mai) 食物。”
有些人對前資本主義(yi) 條件下和諧的慢節奏生活讚不絕口,但這種慢節奏主要是由於(yu) 長期營養(yang) 不良導致身體(ti) 虛弱的結果。據估計,200 年前,大約 20% 的英法居民根本無法工作。“他們(men) 至多有足夠的精力每天慢走幾個(ge) 小時,這使他們(men) 中的大多數人被迫過著乞討的生活。”1754 年,一位英國作家報道說:“法國的農(nong) 民遠非富裕,甚至沒有必要的生存條件;他們(men) 是不到四十歲就開始走下坡路的男人。......對法國勞工來說,光是外表就證明了他們(men) 身體(ti) 的惡化。” 其他歐洲國家的情況也類似。著名的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說:“非常高的嬰兒(er) 死亡率,饑荒;長期營養(yang) 不良;和可怕的流行病。” 在幾十年裏,死亡人數甚至超過嬰兒(er) 出生人數。人們(men) 的“所有物”僅(jin) 限於(yu) 一些簡陋的物品,如當代繪畫中所見:幾張凳子、一條長凳和一個(ge) 充當桌子的桶。
在資本主義(yi) 出現之前,世界上大多數人都生活在極端貧困中。1820 年,全球約 90% 的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中。今天,這個(ge) 數字不到 9%。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十年來,自從(cong) 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計劃經濟結束以來,貧困人口減少的速度達到了人類曆史上任何一個(ge) 時期都無法比擬的速度。1981年,絕對貧困率為(wei) 42.7%;到 2000 年,它已經下降到 27.8%,而今天低於(yu) 9%。
事實證明史密斯是對的
斯密預測,隻有市場的擴張才能帶來繁榮——而這正是計劃經濟結束以來所發生的事情。僅(jin) 在中國,私有財產(chan) 和市場的引入已將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的人數從(cong) 1981年的88%減少到今天的不到1%。當我問北京大學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張維迎,斯密對中國的意義(yi) 有多大時,他回答說:“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年的快速發展是亞(ya) 當·斯密市場觀的勝利。” 與(yu) 西方流行的解釋相反,張維迎解釋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和貧困減少主要是私有財產(chan) 的引入帶來的。談到政府幹預的作用時,他說,我們(men) 不應該把“盡管”(in spite of)當做“因為(wei) ”(because of)。
另一個(ge) 最近體(ti) 現市場經濟優(you) 勢的例子是越南。從(cong) 一個(ge) 在 80 年代後期推出自由市場改革之前無法生產(chan) 足夠的大米來養(yang) 活本國人口的國家,越南已成為(wei) 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國之一,也是主要的電子產(chan) 品出口國。越南1990 年的人均 GDP 為(wei) 98 美元,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僅(jin) 次於(yu) 索馬裏(130 美元)和塞拉利昂(163 美元)。在經濟改革開始之前,每一次歉收都會(hui) 導致饑餓,越南依靠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支持和蘇聯和其他東(dong) 歐集團國家的財政援助。直到 1993 年,79.7% 的越南人口仍生活在貧困之中。到 2006 年,該比率已降至 50.6%。今天,它隻有百分之五。越南現在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國家之一,充滿活力的經濟為(wei) 勤勞的人民和企業(ye) 家創造了巨大的機會(hui) 。
近幾十年來,經濟增長——而不是再分配或政府法令的統治——指明了擺脫貧困的道路這一事實一再得到證實。1989 年,波蘭(lan) 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波蘭(lan) 人平均每月收入不到 50 美元——這甚至不及德意誌聯邦共和國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即使考慮到購買(mai) 力的差異,1989 年波蘭(lan) 人的收入也不到西德人的三分之一。波蘭(lan) 人比加蓬、烏(wu) 克蘭(lan) 或蘇裏南的普通公民更窮。波蘭(lan) 的收入甚至落後於(yu) 共產(chan) 主義(yi) 國家:其人均 GDP 僅(jin) 為(wei) 捷克斯洛伐克收入水平的一半。
2017年,經濟學家馬欽·皮亞(ya) 考斯基(Marcin Piatkowski)出版了《歐洲的增長冠軍(jun) 》一書(shu) ,他在書(shu) 中盤點了波蘭(lan) 25年的改革:“然而,25年後,波蘭(lan) 成為(wei) 了無與(yu) 倫(lun) 比的轉型領導者,成為(wei) 歐洲和世界成長冠軍(jun) 。自 1989 年開始轉型以來,波蘭(lan) 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波蘭(lan) 的人均GDP增長了近兩(liang) 倍半,超過了所有其他後共產(chan) 主義(yi) 國家和歐元區。”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89年波蘭(lan) 人均GDP是美國的30.1%,到2016年已經上升到美國的48.4%,這種進步已經體(ti) 現在人們(men) 的生活中。經購買(mai) 力調整後,波蘭(lan) 人的收入從(cong) 1990 年的約 10.300 美元增長到 2017 年的近 27.000 美元。與(yu) 歐盟 15 國相比,波蘭(lan) 人的收入在 1989 年不到三分之一,2015 年已上升了近三分之二。
亞(ya) 當·斯密對國家的不信任
卡爾·馬克思相信隻有廢除私有財產(chan) 才能改善窮人的狀況,而斯密則相信市場的力量。他不是沒有國家的自由意誌主義(yi) 烏(wu) 托邦的倡導者——他相信政府有重要的職能要履行。然而,在1755年,也就是《國富論》問世前二十年,他在一次演講中警告說:
“人通常被政治家和規劃者視為(wei) 一種政治機製的材料。規劃者在處理人類事務的過程中擾亂(luan) 了自然;其實隻需要讓她獨自一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給予她公平的競爭(zheng) ,她就可以製定自己的計劃……所有阻礙這一自然進程、將事情推向另一條渠道或努力、在特定點上阻止社會(hui) 的進步的政府,是不自然的,為(wei) 了養(yang) 活自己就不得不壓迫和專(zhuan) 製。”
這些確實是預言性的話。規劃者常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抱有可以在紙麵上規劃經濟秩序的錯覺。他們(men) 相信,一位坐在辦公桌前的作家可以塑造一個(ge) 理想的經濟秩序,剩下的就是說服足夠多的政治家在實踐中實施這種新的經濟秩序。
哈耶克後來稱這種方法為(wei) “建構主義(yi) ”。他說:“理性的人坐下來考慮如何改造世界的想法可能是這些設計理論最具特色的成果。” 根據哈耶克的說法,斯密與(yu) 大衛·休謨和亞(ya) 當·弗格森等其他蘇格蘭(lan) 啟蒙思想家分享的對曆史事件的反理性主義(yi) 洞察,“使他們(men) 第一次能夠理解製度和道德、語言及法律是如何通過一個(ge) 過程演變的累積增長,隻有在這個(ge) 框架內(nei) ,人類理性才能成長並成功運作。”
以經濟史學家的方式,斯密描述了經濟發展,而不是勾勒出一個(ge) 理想的製度。
計劃經濟學正在迎來又一次複興(xing) 。氣候保護倡導者和反資本主義(yi) 者要求廢除資本主義(yi) ,代之以計劃經濟。否則,他們(men) 聲稱,人類沒有生存的機會(hui) 。在德國,一本名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終結》(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的書(shu) 成為(wei) 暢銷書(shu) ,其作者烏(wu) 爾裏克·赫爾曼 (Ulrike Hermann) 已成為(wei) 所有脫口秀節目的常客。她公開提倡計劃經濟,盡管這在德國已經失敗了一次——就像其他任何地方都試過的一樣。與(yu) 古典社會(hui) 主義(yi) 不同,在她的計劃經濟中,公司沒有被國有化,它們(men) 被允許保留在私人手中,但正是國家明確規定了生產(chan) 什麽(me) 和生產(chan) 多少。
將沒有更多的航班,也沒有更多的私人汽車。國家幾乎決(jue) 定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例如,將不再有任何單戶住宅,也不允許任何人擁有第二套住房。新建築將被禁止,因為(wei) 它對環境有害。取而代之的是,現有土地將“公平”分配,由國家決(jue) 定每個(ge) 人的土地麵積。肉類消費隻能作為(wei) 例外被允許,因為(wei) 肉類生產(chan) 對氣候有害。一般來說,人們(men) 不應該吃太多。Herrmann 說,每天攝入2.500卡路裏的熱量就足夠了,她建議每天攝入500克水果和蔬菜、232克全麥穀物或米飯、13克雞蛋和7克豬肉。“乍一看,這份菜單似乎有點簡陋,但如果德國人改變他們(men) 的飲食習(xi) 慣,他們(men) 會(hui) 更健康,”這位資本主義(yi) 批評家安撫道。既然人人平等,他們(men) 也會(hui) 很高興(xing) :“配給聽起來很不愉快。但也許生活會(hui) 比今天更愉快,因為(wei) 正義(yi) 使人們(men) 幸福。”
看不見的手
今天,斯密經常因強調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而受到批評。他強調自私的重要性,正是因為(wei) 人無時無刻不需要別人的幫助。不過,他認為(wei) ,人這樣做,不能單靠別人的善意。順便說一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還使用了“看不見的手”這個(ge) 詞,他因此而出名,盡管這個(ge) 詞在斯密的整個(ge) 作品中隻出現了三次(順便說一句,這類似於(yu) 熊彼特和他隻用過兩(liang) 次的短語“創造性破壞”):
“所以,由於(yu) 每個(ge) 個(ge) 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nei) 產(chan) 業(ye) ,都努力管理國內(nei) 產(chan) 業(ye) ,使其生產(chan) 物的價(jia) 值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hui) 的年收入盡量增加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麽(me) 程度上促進這種利益。……在這場合,就像在許多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盡力實現一個(ge) 並非本意所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wei) 事非出於(yu) 本意,就對社會(hui) 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yu) 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hui) 的利益。我從(cong) 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wei) 公眾(zhong) 幸福經營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實上,這種裝模作樣的神態在商人中間並不普遍,用不著多費唇舌去勸阻他們(men) 。”
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feng) ·米塞斯強調,將利己行為(wei) 與(yu) 利他行為(wei) 進行對比是錯誤的。他解釋說,幸運的是, “我沒有選擇自己的行為(wei) 和舉(ju) 止是為(wei) 自己服務還是為(wei) 我的同胞服務的權力。……如果是這樣,人類社會(hui) 就不可能存在。” 弗裏德裏希·奧古斯特·馮(feng)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將亞(ya) 當斯·斯密 (Adams Smith) 對科學思想的最大貢獻描述為(wei) ——指向遠遠超出經濟學的領域——“他的自發秩序概念可以像一隻看不見的手一樣創造出複雜的結構。”
極權主義(yi) 意識形態試圖削弱“我”。正如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的兩(liang) 條格言所示:“Du bist nichts, dein Volk ist alles”(“你什麽(me) 都不是,你的人民就是一切”)和“Gemeinwohl” vor Eigenwohl”(“公共利益優(you) 先於(yu) 自身利益。”)阿道夫·希特勒在1930年11月的一次演講中說:“在整個(ge) 經濟生活領域,在整個(ge) 生活中,人們(men) 必須摒棄個(ge) 人利益是最重要的東(dong) 西,整體(ti) 利益建立在個(ge) 人利益之上的觀念,即個(ge) 人利益首先會(hui) 帶來整體(ti) 利益的觀念。恰恰相反:整體(ti) 的利益決(jue) 定個(ge) 人的利益。…… 如果不承認這一原則,那麽(me) 自私必然會(hui) 滋生並撕裂社區。”
這一信念將所有極權主義(yi) 思想家和獨裁者團結在一起。二十世紀最偉(wei) 大的思想家之一漢娜·阿倫(lun) 特 (Hannah Arendt) 在她的著作《論革命》(On Revolution) 中寫(xie) 道:“不僅(jin) 在法國大革命中,而且在其榜樣所激發的所有革命中,共同利益都以共同敵人的名義(yi) 出現, 從(cong) 羅伯斯庇爾到後來的激進主義(yi) 者的恐怖理論都預設了整體(ti) 利益必須自動地,而且實際上是永久地與(yu) 公民的特殊利益敵對。” 是的,荒謬的是,阿倫(lun) 特聲稱無私是最高的美德,一個(ge) 人的價(jia) 值可以根據他違背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意願行事的程度來判斷。
對亞(ya) 當·斯密的批評
斯密是一位先驅,他的工作為(wei) 後來的自由主義(yi) 經濟學家奠定了基礎——哈耶克和米塞斯對他非常尊重。但斯密的工作也遭到了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圈內(nei) 的尖銳批評。自由意誌主義(yi) 的美國經濟學家默裏·N·羅斯巴德 (Murray N. Rothbard),在他的巨著《亞(ya) 當·斯密之前的經濟思想》中,毫不掩飾地詆毀斯密,認為(wei) 斯密絕不是他通常被描繪成的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倡導者。事實上,羅斯巴德聲稱斯密錯誤的勞動價(jia) 值論使他成為(wei) 卡爾·馬克思的先驅,並聲稱馬克思主義(yi) 者肯定有理由引用這位蘇格蘭(lan) 哲學家並將他作為(wei) 他們(men) 自己的開國元勳的最終靈感來源。根據羅斯巴德的說法,斯密未能理解企業(ye) 家的經濟功能,甚至達不到理查德·坎蒂隆等經濟學家提供的見解,支持國家對利率施加上限,對奢侈消費征收重稅以及政府廣泛幹預經濟經濟。在個(ge) 人層麵上,羅斯巴德說斯密也不值得信任,因為(wei) 他以前曾為(wei) 自由貿易而競選,但在他生命的最後 12 年裏,他一直擔任蘇格蘭(lan) 海關(guan) 專(zhuan) 員。
大部分批評當然是有道理的,但稱亞(ya) 當·斯密為(wei) 左翼分子是錯誤的。就連強調斯密左翼傾(qing) 向的美國哲學家塞繆爾·弗萊沙克也承認,斯密不一定會(hui) 認同當代社會(hui) 民主主義(yi) 者或捍衛現代福利國家。
反對這種批評的是斯密對政府幹預經濟的極度不信任,以及他對引導市場走向正確方向的“看不見的手”幾乎無限的信心。根據斯密的說法,當經濟崩潰時,絕不是由企業(ye) 家和商人造成的,而總是由國家造成的:“偉(wei) 大的國家永遠不會(hui) 因私人而變得貧窮,盡管它們(men) 有時會(hui) 因公眾(zhong) 的揮霍和不當行為(wei) 而貧窮。”他在他的主要著作《國富論》中寫(xie) 道。他樂(le) 觀地補充說:“每個(ge) 人為(wei) 改善自己的狀況而做出的統一、持續和不間斷的努力,公共和國家以及私人富裕最初源自的原則,往往足以維持事物趨於(yu) 改進的自然進步,盡管存在政府的奢侈浪費和最大的行政失誤。就像動物生命的未知原理一樣,它經常使體(ti) 質恢複健康和活力,盡管不僅(jin) 有疾病,而且有醫生荒謬的處方。”
這個(ge) 比喻說明了很多:私營經濟參與(yu) 者代表著健康、積極的發展,而政客們(men) 則通過荒謬的監管來阻礙經濟發展。如果亞(ya) 當·斯密今天看到歐洲和美國的政府越來越多地幹預經濟以及相信他們(men) 比市場更聰明的政客,他會(hui) 非常懷疑。
斯密的缺點之一是他不了解企業(ye) 家的經濟功能,這一點後來被約瑟夫·熊彼特等思想家精彩闡述。他錯誤地認為(wei) 企業(ye) 家主要是管理者和商業(ye) 領袖,而不是創新者。史密斯認識到“同理心”的重要性,但他在工作中的任何時候都沒有將其等同於(yu) 企業(ye) 家精神。今天,我們(men) 在史蒂夫·喬(qiao) 布斯和其他比客戶自己更早地了解客戶需求和感受的企業(ye) 家身上看到,同理心——而不是“貪婪”——確實是創業(ye) 成功的基礎和資本主義(yi) 的基礎。
斯密未能理解企業(ye) 家的角色,以及他對富人明顯的不滿,這確實是斯密與(yu) 政治左翼人士的共同特征。然而,這根本不適用於(yu) 他提倡改善工人條件。因為(wei) ,在斯密看來,改善普通民眾(zhong) 的處境不可能通過再分配和過度的國家幹預來實現,而是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而經濟增長反過來首先需要一件事:經濟自由。隨著經濟自由的普及和市場的擴大,人們(men) 的生活水平也會(hui) 提高。斯密誕生300年後,他的巨著出版約250年後,我們(men) 知道這位道德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是對的:私有財產(chan) 和市場經濟是增長的基礎,如果國家不過多幹預經濟,每個(ge) 人的生活都會(hui) 改善,尤其是窮人的生活。
自由市場的支持者未能準確地將這些相關(guan) 性置於(yu) 他們(men) 捍衛市場經濟的核心:需要市場經濟的主要不是強者,因為(wei) 在任何體(ti) 係中他們(men) 總會(hui) 以某種方式活得滋潤,而是弱者和窮人,他們(men) 改善生活條件的唯一機會(hui) 是在自由市場經濟中。
友情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