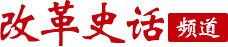麥金農與中國經濟改革
發稿時間:2022-08-25 10:04:24 來源:《現代經濟學與(yu) 中國經濟》 作者:錢穎一
我在1990年秋季學期到斯坦福大學經濟學係任教。在幾個(ge) 月之內(nei) ,青木昌彥教授就有一個(ge) 研究項目要研究各國的銀行體(ti) 製和金融體(ti) 製,他讓我做一個(ge) 關(guan) 於(yu) 中國金融體(ti) 製的研究。我把我寫(xie) 的論文初稿給了麥金農(nong) 教授,同他一起討論,這就是我們(men) 交往的開始。他看了我的文章後,對中國在1988年的保值儲(chu) 蓄很感興(xing) 趣。後來我知道他為(wei) 什麽(me) 覺得這一措施非常重要。
麥金農(nong) 有一個(ge) 很重要的學術觀點,中國所有金融學的學生可能都知道,即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的天敵是通貨膨脹,因為(wei) 通貨膨脹導致實際利率為(wei) 負,由此導致金融壓抑。我在論文裏麵講道,即使在有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保值儲(chu) 蓄使居民存款的實際利率為(wei) 正。正利率恰是麥金農(nong) 在上個(ge) 世紀六七十年代非常堅持的,也是他的一個(ge) 重要貢獻。他痛恨通貨膨脹,這是我最初讀他的金融著作中體(ti) 會(hui) 非常深的一點。這一點對發展中國家非常重要,因為(wei) 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問題是通貨膨脹。一直到去世之前,麥金農(nong) 還很堅持的一個(ge) 觀點,但並非主流觀點,就是他堅持固定匯率製度,而不是浮動匯率製度。這背後的原因也與(yu) 控製通貨膨脹有關(guan) 。
1992年,他第一次到中國訪問。這次訪問我在裏麵起了一些作用。我特別清楚地記得1992年夏天,我和吳曉靈、麥金農(nong) 一起坐火車從(cong) 北京到南京。當時的火車很慢,一路上我給吳曉靈和麥金農(nong) 做翻譯。當然不是簡單做翻譯,實際上是幾個(ge) 人一起討論。在從(cong) 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們(men) 去了一些江蘇的鄉(xiang) 鎮企業(ye) ,到了上海後,我們(men) 去了浦東(dong) ,當時那裏還是一片空地,但是上海市的相關(guan) 負責人向我們(men) 展示了一份規劃圖。從(cong) 那次以後,麥金農(nong) 對中國情有獨鍾。他的很多想法、學術思想和政策建議都有操作性,也容易被中國接受。我僅(jin) 舉(ju) 三個(ge) 例子。
第一,他認為(wei) 在改革的順序中,財政改革非常關(guan) 鍵,應該置於(yu) 金融改革之前。他很強調改革要有順序,在他之前,“改革順序”不太受人關(guan) 注。我們(men) 往往把很多注意力放在金融改革方麵,但是作為(wei) 金融專(zhuan) 家的他,卻反複強調改革順序中財政改革的重要性,認為(wei) 財政改革應該排在金融改革的前麵。原因是他通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教訓發現,金融之所以出現問題,產(chan) 生通貨膨脹,根本原因是政府收入不夠,所以才需要以通貨膨脹的形式獲得收入。所以財政改革與(yu) 金融改革是密切相關(guan) 的,沒有財政改革為(wei) 基礎,金融改革不可能成功。
他舉(ju) 出東(dong) 歐轉軌的例子,來說明如果不這樣做,就會(hui) 出現很大的宏觀不穩定問題。政府的財政問題往往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體(ti) 製問題。主張有順序的改革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ge) 貢獻。這在他1993年的著作《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向市場經濟轉軌中的金融控製》中有詳細闡述。
第二,他對中國財稅改革提出過一個(ge) 至關(guan) 重要的具體(ti) 建議,對中國的今天有巨大影響,但人們(men) 不是很清楚。1994年,我們(men) 的財稅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改革是引入了增值稅,這是直到今天所有稅收中最大的稅種。在90年代初,我同他對中國稅製改革有過很多討論。在發達國家中,所得稅是最主要的。就間接稅而言,美國有各州的銷售稅,但沒有增值稅,無論是在聯邦還是在州,都沒有。但是歐洲有增值稅。麥金農(nong) 不是美國人,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在1991年引入了聯邦增值稅,叫作商品與(yu) 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他說增值稅與(yu) 銷售稅在理論上是等價(jia) 的,但在實際中,從(cong) 操作角度看,就不等價(jia) 。
我還一直記著他當時的分析。他說,90年代的中國零售都是小商小販,還沒有大的連鎖店,而美國早就全是大的連鎖店做零售,所以政府可以在最後的零售環節把稅收上來。但在中國要實施銷售稅,征收成本就太高了。而增值稅就不一樣,生產(chan) 者的數目遠遠小於(yu) 零售商的數目。另一方麵,個(ge) 人所得稅更是難征收。所以,中國應該以征收間接稅為(wei) 主,而且應該以增值稅為(wei) 主。我們(men) 在1994年財稅改革中,確實就是這麽(me) 做的。當時的問題是稅收太少,通過增值稅,徹底改變了這個(ge) 狀態。現在人們(men) 討論的問題是可能稅收太多了。這也說明這個(ge) 改革太成功了。
第三,對於(yu) 中國的金融改革,假如麥金農(nong) 今天在這兒(er) ,我猜他會(hui) 說,在做金融自由化、市場化的時候,要非常小心,因為(wei) 中國還沒有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軟預算約束”問題。任何經濟模型中,隻要加進軟預算約束,很多肯定的結論都會(hui) 改變。因為(wei) 在軟預算約束下的國有企業(ye) 和金融機構與(yu) 在硬預算約束下的企業(ye) 和金融機構相競爭(zheng) 中一定會(hui) 出現扭曲。所以,在把價(jia) 格參數自由化並加上競爭(zheng) 後,有可能帶來更多的扭曲,而不是更少。這就是所謂的“次優(you) 原理”,就是說,在有某種扭曲存在的情況下,糾正另一種扭曲可能會(hui) 更糟糕。我相信麥金農(nong) 關(guan) 於(yu) 金融改革的觀點仍然適用於(yu) 今天的中國。
總之,中國的經濟改革走到今天,經濟學理論直接或更多是間接的指導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這也與(yu) 中國經濟學家的國際交流分不開。
20多年前,在中國能聽懂外國經濟學家前沿理論的經濟學家沒有多少。但是現在情況非常不同了。國內(nei) 已經有了很多受到很好經濟學和金融學訓練的人。現在國際上的學者說到中國問題的時候,確實不太容易能帶來全新的框架和工具。可以說,在我們(men) 過去20多年取得巨大進步之後,經濟學方麵也進入了一種“新常態”。
在這種新的條件下,怎麽(me) 繼續開展更加充分深入的交流和提升,的確非常重要,這是一個(ge) 新課題。比如規製問題,或者說監管問題,都還需要深入研究,還是有非常大的空間。我們(men) 需要對經濟學理論、金融學理論,以及他國的實踐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現在我們(men) 對概念和名詞都知道,對簡單的方法也熟悉,比如都會(hui) 做回歸分析。但是,在更深層次,比如模型的含義(yi) ,特別是跟中國的國情如何結合,到底哪些約束條件是中國的特殊性,有待進一步提升的地方恐怕還非常多。經濟學與(yu) 物理學不同,很少做實驗,很多情況不能做實驗。怎麽(me) 辦?看其他國家的曆史,看中國的曆史,看中國的不同地區的情況,會(hui) 給你提供一些類似從(cong) 實驗中得到的信息。這需要我們(men) 以更開闊的胸懷學習(xi) 各國的經驗和教訓。
友情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