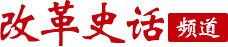18世紀英國怎麽看中國園林
發稿時間:2021-03-01 14:03:27 來源:學習(xi) 時報 作者:胡淼森
18世紀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黃金時期。隨著17世紀法國耶穌會(hui) 士陸續入華,中國的禮儀(yi) 、法律、製度、科技等知識傳(chuan) 播到歐洲大陸,成為(wei) 歐洲啟蒙運動的催化劑。孔子的儒家精神,刺激著西方人走出神學時代而步入啟蒙,同時中國的器物、藝術乃至抖空竹等民間遊戲都進入了西方並產(chan) 生了持續影響。在藝術品和器物領域,西方人愛不釋手地把玩欣賞中國茶具、屏風、扇子,中國元素影響到教堂、花園和室內(nei) 裝潢的藝術風格。
打破古典主義(yi) 回到自然風致
在“中國熱”中,中國園林的一些特點以文字和裝飾畫的方式傳(chuan) 入了歐洲,在整個(ge) 歐洲引發轟動,這一時期古典主義(yi) 的巴洛克藝術漸趨衰亡,而洛可可藝術在“中國熱”的推動下風靡一時。在英國,經過坦普爾、艾迪生等人的介紹和坎特、勃朗等人的設計,中國園林同英國人對自由無束景象的熱愛融匯起來,產(chan) 生了所謂“自然風致園”,特點是將花園布置得像田野牧場一樣,就像從(cong) 鄉(xiang) 村的自然界裏取來的一部分。
中國園林在英國掀起了園林熱。從(cong) 當時設計的疊石假山、山洞拱橋以及18世紀坎布裏奇和沃爾等建築師留下的文字中可以推斷,18世紀上半期英國出現的自然風致園受到中國園林較大影響。
巧奪天工賞心樂(le) 事
18世紀後半期,中國園林的影響進入第二階段,錢伯斯爵士依據中國園林風格設計的“丘園”是“圖畫式園林”的典型代表,甚至開始援引中國園林來指責自然風致園。
歐洲人對於(yu) 中國園林的了解渠道還不多,王致誠寫(xie) 於(yu) 1743年的信件介紹了位於(yu) 北京海澱的暢春園、圓明園、綺春園和長春園。王致誠以畫家的眼光發現了中國園林的自然天成之美,宛如“大自然那鬼斧神工的傑作”,沒有筆直的甬道,而多是彎曲的盤旋路和羊腸小道。這段文字在進入歐洲後,對當時的園林建造觀念造成一定的衝(chong) 擊。王致誠的介紹十分詳盡,且初步涉及中國園林的某些美學特征,遺憾的是未能深入揭示中國園林背後的某種精神,回答“中國人為(wei) 什麽(me) 要這樣建造園林”的問題,未能揭示中國人如此運用寫(xie) 意技術的真諦。
不過,《中國雜纂》中收錄了兩(liang) 篇韓國英的信件,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園林有更深入的認識。韓國英也是一位畫家,據說他同一個(ge) 叫劉舟的中國人切磋過中國造園藝術。韓國英的閃光點在於(yu) 第一封信,他翻譯了司馬光關(guan) 於(yu) “獨樂(le) 園”的長詩,並附上他本人的一篇短文介紹中國園林;第二封信題名為(wei) 《論中國園林》,概述了中國造園史和造園藝術的原則。
也許受劉舟的影響,韓國英試圖用中國人司馬光的作品來解釋園林的功用,但他用詩體(ti) 譯成的這首《獨樂(le) 園》的長詩,卻不見於(yu) 司馬光的各種詩文集,與(yu) 其意思接近的是司馬光的散文《獨樂(le) 園記》。《獨樂(le) 園記》中確有一段話表達出重視獨處與(yu) 靜思的念頭:“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複有何樂(le) 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le) 園’。”韓國英在《論中國園林》中強調中國園林對於(yu) 心靈寧靜的營造:“還要想到,人們(men) 到園林裏來是為(wei) 了避開時間的煩擾,自由地呼吸,在沉寂獨處中享受心靈和思想的寧靜,人們(men) 力求把花園做得純樸而有鄉(xiang) 野氣息,使它能引起人的幻想。”由此看來,他應該是讀過司馬光《獨樂(le) 園記》原文的。
傳(chuan) 教士對園林藝術的介紹缺乏相應文學的支撐,也就使得中國園林的真實麵目被西方人有意無意間誤解。英國人選擇中國園林作為(wei) 自然風致園的模板,也經曆了一定的文化過濾和改造。在法國傳(chuan) 教士對於(yu) 中國園林的相關(guan) 文學作品保持沉默的前提下,英國人卻經由中國園林強化了自身對於(yu) “荒野”的迷戀,甚至將中國園林與(yu) 恐怖、驚異乃至崇高這樣的審美心理聯係在一起,掀起了一陣“誤讀的盛況”。
中國園林之美
相比於(yu) 同時期的古典主義(yi) 法國,英國更為(wei) 重視感性和自然的因素。但英國人心中的自然與(yu) 中國人的自然不太一樣,英國人更迷戀“荒野”的氣氛,強調野趣、自由、奔放甚至有些恐怖的場景,對於(yu) 大自然的迷戀與(yu) 神話、傳(chuan) 說、顯赫的曆史結合在一起,在狂放的自然中完成對於(yu) 個(ge) 體(ti) 自由的確認;中國人則關(guan) 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這樣的和諧境界,追求的是“物我兩(liang) 忘”“陶然共忘機”的和諧狀態。
在18世紀,英國人卻沒有注意這個(ge) 差別,從(cong) 坦普爾到錢伯斯,這些英國造園家從(cong) 未看過真正的中國園林,而是從(cong) 自身傳(chuan) 統出發,對於(yu) 中國園林做出了種種臆想和推斷。錢伯斯在1757年出版的《中國建築、家具、服裝和器物的設計》一書(shu) 中,開篇指出中國園林的基本特點:大自然是他們(men) 的仿效對象,他們(men) 的目的是模仿它的一切美麗(li) 的無規則性;中國園林重視整體(ti) 、剪裁和提煉等特征。但論到園林中“景的性情”的分類,他說,“他們(men) 的藝術家把景分為(wei) 三種,分別稱為(wei) 爽朗可喜之景、怪駭驚怖之景和奇變詭譎之景”。這一點則是他者的眼光,需要中國人進一步去理解。
所謂的“怪駭驚怖之景”,中國園林中即使有,也應該是極少數的另類,大概隻存在於(yu) 錢伯斯的想象中。這樣強調恐怖,其實就是英國人乃至整個(ge) 西歐文明對待荒野的既恐懼又迷戀的集體(ti) 無意識。這種西式思維,根源於(yu) 從(cong) 朗吉努斯再到博克等西方哲學家對於(yu) “崇高”與(yu) “優(you) 美”的二分。
博克認為(wei) “驚懼是崇高的基本原則”,他在1756年發表的《論崇高和美的觀念的起源》中,對崇高下了如下定義(yi) :凡是能以某種方式適宜於(yu) 引起苦痛或危險觀念的事物,即凡是能以某種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對象的,或是類似恐怖那樣發揮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個(ge) 來源。錢伯斯毫無根據的臆想卻引起了博克的注意,1758年,博克自己主編的《年鑒》中甚至轉載了前述1757年錢伯斯的那篇文章,試圖將錢伯斯描繪的“怪駭驚怖之景”作為(wei) 例證納入到自己對於(yu) 自然界崇高之美的理論體(ti) 係中。正是在種種奇特的轉譯與(yu) 文化誤讀之下,中國園林成為(wei) 了“崇高”美學風格的化身。
中國園林的本來麵目更接近於(yu) “優(you) 美”而非“崇高”,它有著洛可可藝術式的優(you) 雅與(yu) 日常,不是靠驚駭與(yu) 恐怖來征服遊園者的,而是孕育著悠久的文人雅致,這一點英國人很難一下子理解。
在中國園林影響最大的英國,18世紀的模仿熱潮中存在著對於(yu) 中國藝術與(yu) 文化精神的嚴(yan) 重誤讀,將其特征定位為(wei) 崇高與(yu) 驚懼,顯示出了巨大的文化隔閡。在此隔閡之下,西方完成了一次對於(yu) 中國和遠東(dong) 藝術的想象。園林的實質是文人化的藝術,是中國文人寄意山水田園、尋求自然雅趣的結果,中國詩詞歌賦中遍布對於(yu) 田園、山水、風景與(yu) 歸隱生活的讚歎,倘能多為(wei) 西人所知,當不至於(yu) 郢書(shu) 燕說到如此地步,也會(hui) 少一些在曆史細節麵前悵然若失的遺憾。
友情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