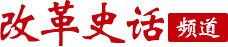麵對瘟疫,人類應該以理性超越指責
發稿時間:2020-05-22 13:52:26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臘碧士 李雪濤
思考全球疫情背後不同的治理邏輯
李雪濤:臘碧士教授好,非常高興(xing) 我們(men) 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討論新冠肺炎與(yu) 疾病史的話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來勢之洶,造成的影響之大,帶來的災難後果之嚴(yan) 重,都是歐洲自二戰以來所未曾遭遇過的。近日您與(yu) 杜塞爾多夫大學醫學史研究所所長房格勞(Heiner Fangerau)教授出版了近200頁的新著《鼠疫和新冠病毒:曆史、現在和未來的全球傳(chuan) 染病》,係統探討了這場全球風暴背後的曆史隱喻、現實指涉與(yu) 未來啟示,為(wei) 我們(men) 深入理解全球疫情背後不同的治理邏輯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視角。
臘碧士:謝謝。這本小書(shu) 實際上是我多年前《衛生人:近代的健康與(yu) 醫學》專(zhuan) 著的“現實版”而已,它所涉及的並非僅(jin) 僅(jin) 是鼠疫和新冠病毒,而是各類社會(hui) 、政治家、行政人員、醫生和研究者如何看待這種極具危險性的瘟疫,在不同文化特色的地區采取怎樣的方式來遏製病毒的蔓延。
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迫使人類必須麵對這樣一個(ge) 事實——我們(men) 習(xi) 以為(wei) 常的生活方式正在經曆重大衝(chong) 擊。曆史地看,這種由疾病帶來的整體(ti) 性變化和影響不是第一次出現,也不會(hui) 是最後一次。在這個(ge) 特殊的節點上,回望人類集體(ti) 記憶深處,那些曾經發生的烈性傳(chuan) 染病如何深刻改寫(xie) 了公共和私人生活?如何理解每一次變化中各種自然、社會(hui) 、曆史和文化的影響要素與(yu) 相互關(guan) 係?麵對新冠肺炎疫情,人類的社會(hui) 設計和醫療建設應當如何延續或順應?疫情風暴之中的個(ge) 體(ti) 又該如何保留或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問題所具有的重大意義(yi) 不僅(jin) 僅(jin) 存在於(yu) 學理層麵的論證話語,對國家、社區和個(ge) 人的社會(hui) 生活實踐也極具價(jia) 值。這本書(shu) 基本上是圍繞著上述問題進行的解說,尤其結合德國的曆史經驗與(yu) 現實選擇進行了多層次的分析。
科學與(yu) 公共衛生的進步才使得抗疫成為(wei) 可能
李雪濤:從(cong) 全球健康史的角度來看,1800年前後,全球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僅(jin) 有30歲,一半以上的人還沒有成年就死了,而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當然是感染疫病。而到了2000年,全球人均預期壽命達到了67歲,營養(yang) 攝取的均衡、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政府在公共衛生監督方麵掌握了新技術等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國當代曆史學家奧斯特哈默甚至認為(wei) ,在人的壽命預期方麵,人類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即便今天我們(men) 不得不麵對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與(yu) 以前的情況相比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臘碧士:很遺憾的是,對人類曆史上大部分的瘟疫,我們(men) 隻能通過有限的文獻記載予以“重構”。因此,有些疫情被誇大了,但更多的疫情卻由於(yu) 文獻的殘缺不全,以至於(yu) 其規模和意義(yi) 很容易被忽略。如果說之前的瘟疫還都是區域性的話,那麽(me) 14世紀的鼠疫席卷了整個(ge) 亞(ya) 歐大陸。進入19世紀後,盡管防疫的措施得到了加強,但瘟疫的傳(chuan) 播速度、傳(chuan) 染力和致病力都進一步加強。從(cong) 1892至1893年發生在漢堡的瘟疫開始,人類才留下詳盡的文獻資料,因為(wei) 這個(ge) 時期的社會(hui) 統計學水平較前已有大幅度的提高。接下來1894至1938年間全球死於(yu) 鼠疫的人口大約有1300多萬(wan) ,而死於(yu)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人數更是多達5000萬(wan) 到1億(yi) ,甚至超出了一戰中的死亡人數。其實我們(men) 耳熟能詳的很多歐洲近代名人都是被瘟疫奪去了生命,隻是我們(men) 以往沒有從(cong) 這個(ge) 角度關(guan) 注過而已——英國詩人濟慈、波蘭(lan) 作曲家肖邦、英國文學家史蒂文森、俄國文學家契訶夫、德語作家卡夫卡,他們(men) 都死於(yu) 結核病;而哲學家黑格爾和普魯士陸軍(jun) 元帥格奈森瑙則殞命於(yu) 1830至1832年的霍亂(luan) 。今天我們(men) 依然很難想象當時普通感染者絕望無助的慘狀。
李雪濤:20世紀90年代初,您在《衛生人:近代的健康與(yu) 醫學》一書(shu) 中首次使用了“令人不安的疾病”一詞,指稱那些在公共空間產(chan) 生的影響與(yu) 流行病學的含義(yi) 不一樣的疾病,正是這樣的一些疫病會(hui) 成為(wei) 社會(hui) 的真正殺手。當前,正是由於(yu) 這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人們(men) 才產(chan) 生了憂慮、畏懼的心態。
臘碧士:是的,從(cong) 人類曆史看,此類“令人不安的疾病”的可怕性在於(yu) 人有一種對未知事物的恐懼。以天花為(wei) 例,1796年英國醫生琴納成功研製出了牛痘疫苗,才使得這種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傳(chuan) 染病不再是人類的殺手,但真正改變局麵的是全民強製接種。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甚至認為(wei) ,拿破侖(lun) 戰爭(zheng) 之所以能取勝,從(cong) 而使法國迅速崛起、雄霸歐洲,除了軍(jun) 事製度的重大變化和火炮的使用外,最重要的原因在於(yu) 早在1800年拿破侖(lun) 便下令在全國實行強製性接種。在1808至1811年間,法國有近170萬(wan) 人接種了牛痘。
李雪濤:正是這樣。1870年的普法戰爭(zheng) 中,普魯士士兵在奔赴前線時接種了兩(liang) 次牛痘,而法國軍(jun) 隊卻沒有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結果有2萬(wan) 士兵因此失去了作戰能力。給士兵接種疫苗成為(wei) 普魯士取得普法戰爭(zheng) 勝利的“法寶”之一。全民強製免疫當然很重要,但一旦有了疫情,現代醫學會(hui) 采取隔離措施。特別有名的記載是後來成為(wei) 德意誌帝國總參謀長的毛奇元帥的經曆,1836年他作為(wei) 奧斯曼帝國蘇丹王年輕的軍(jun) 事顧問,親(qin) 身經曆了在伊斯坦布爾導致近8萬(wan) 人喪(sang) 生的大瘟疫,在返回德國途中經過奧地利邊境的時候,他不得不接受為(wei) 期10天的“禁閉”。其實在此之前,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區,由政府下令對港口實施隔離已經成為(wei) 一種傳(chuan) 統的習(xi) 慣做法,這就是我們(men) 今天的“隔離”。
臘碧士:從(cong) 曆史來看,歐洲在19世紀進行了關(guan) 鍵的一步改革,那就是不再將公共醫療保障看成是教會(hui) 或者私人的慈善事業(ye) ,而理應是現代政府的一項職責。實際上一直到19世紀80年代,公共衛生領域才由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發展出微生物理論,作為(wei) 細菌學產(chan) 物的“衛生人”概念才產(chan) 生,巴斯德與(yu) 發現結核杆菌的德國細菌學家科赫等人的地位,也從(cong) 科學家上升為(wei) 代表整個(ge) 時代的文化英雄。疾病從(cong) 此擺脫了之前的生態的、社會(hui) 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語境,健康本身被解釋為(wei) 最崇高的價(jia) 值,逐漸為(wei) 更多階層所普遍接受。但從(cong) 全球範圍來看,各國用公共資金修建包括醫院在內(nei) 的各種醫療服務體(ti) 係,其實從(cong) 20世紀才開始。
李雪濤:19世紀末阿司匹林的問世,以及之後全民免疫體(ti) 係的啟用,磺胺類藥物與(yu) 抗生素的使用,使得人們(men) 遠離了大部分的瘟疫。這些基礎,也使得今天的抗疫成為(wei) 可能。
臘碧士:其實,每天死於(yu) 心肌梗死、癌症、各種代謝病等常見疾病的人數常常很令人吃驚。但這些是人們(men) 熟悉的疾病,盡管有著很高的死亡率,也不會(hui) 引起人們(men) 的關(guan) 注。而新冠肺炎則完全不同,今天有關(guan) 疫情的報道遍布各種大眾(zhong) 媒介,也成為(wei) 人們(men) 最主要的談話內(nei) 容。在曆史上,當一個(ge) 好端端的人在極短的時間內(nei) 悲慘地死去,正常的倫(lun) 理道德和神學信仰很快便崩潰了。這種恐懼使得人們(men) 一改往日理性的生活方式,各種享樂(le) 主義(yi) 和具有宿命論色彩的宗教團體(ti) 得道,各種我們(men) 以往認為(wei) 荒誕不經的行為(wei) 都成為(wei) 可能。
李雪濤:也就是說,大的瘟疫往往使以往固定下來的社會(hui) 結構分崩離析,從(cong) 前的價(jia) 值體(ti) 係不複存在,既有的製度和觀念難以維持,之前的生活方式失去意義(yi) 。
現代醫學沒有“有罪者”的概念
李雪濤:我們(men) 再看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德國《明鏡周刊》采訪您時,記者認為(wei) 中國所采取的措施“過分小心”。您當時就指出,中國的情況比較特殊,武漢的情形迫使國家采取非常嚴(yan) 格的措施,這當然也是阻斷傳(chuan) 染源的最有效的傳(chuan) 統方式。你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認為(wei) ?
臘碧士:在談到武漢和中國其他地方“封城”的時候,我也特別提到,這種方式在具有數千年曆史的中國是可以實行,並且能夠堅持下去的。
李雪濤:目前對新冠病毒來源的探索沒有停止,並有被政治化的現象。從(cong) 疾病史的角度來看,很多瘟疫很難追蹤到真正的源頭。以往的曆史學家,一般會(hui) 將歐洲黑死病的起因歸結到中國,但澳大利亞(ya) 曆史學家費克光卻根據大量中文文獻,對鼠疫曾在中國發生並且從(cong) 中國傳(chuan) 到歐洲的普遍看法提出了質疑,因為(wei) 僅(jin) 憑古漢語文獻所描述的疫病外在表現特征,是沒有辦法來認定元代流行的疫病就是鼠疫的。霍亂(luan) 在1817年成為(wei) 大流行病之後,全世界都在探求這一疫病的來源。香港大學的程凱禮認為(wei) ,盡管Cholera Asiatica(亞(ya) 洲霍亂(luan) )的漢語被翻譯成“霍亂(luan) ”,但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這種疫病就是源自古代漢語、使用了三千年之久的“霍亂(luan) ”一詞所指的疾病。其實早在1933年,時任上海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的著名鼠疫專(zhuan) 家伍連德就曾發表英文論文,對這一問題進行過權威性的調查。經過細致的對比,伍連德認為(wei) 當時大流行的霍亂(luan) 與(yu) 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霍亂(luan) ”其實是兩(liang) 種不同類型的疫病。
臘碧士:您觀察到了問題。我記得很清楚,2009至2010年的H1N1型禽流感在德國造成了大約23萬(wan) 人感染,有據可查的死亡案例為(wei) 250人。而實際的數字,不論是感染人數,還是死亡人數,肯定要大大超出這些。但我們(men) 當時並沒有對這件事情產(chan) 生過分的反應。H1N1禽流感來源於(yu) 美國,但當時我們(men) 並沒有譴責美國。不論是今天還是以往,在發生疫情的地方,當地人往往指責“他者”:在歐洲中世紀是指責猶太人,20世紀以來則指責東(dong) 南亞(ya) 的華人。人們(men) 自覺或不自覺地去尋找所謂的有罪者,但現代醫學中沒有“有罪者”這樣的概念。
國際學者都可從(cong) 中方研究成果中受益
李雪濤:14世紀,在鼠疫流行的時代,猶太人在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遭到人們(men) 的普遍譴責和攻擊,他們(men) 被認為(wei) 是傳(chuan) 播鼠疫的罪魁禍首。威廉·麥克尼爾曾經對“梅毒”一詞在16世紀時的不同名稱進行過分析,他認為(wei) ,人類普遍有一種把新出現的、險惡的疫病之源頭歸結於(yu) 外國人的傾(qing) 向。霍亂(luan) 在歐洲被稱作“亞(ya) 洲霍亂(luan) ”就曾引發了歐洲人對揣測已久的東(dong) 方災禍的恐懼心理。而19世紀90年代開始引起全球關(guan) 注的鼠疫,由於(yu) 當時被稱作“亞(ya) 洲瘟疫”,在一些地區也發生了過激行為(wei) 。在1898年被美國政府宣布並入美國的火奴魯魯,當地有人為(wei) 了泄憤,縱火燒毀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居住區。在瘟疫流行時期,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臘碧士:信息並不能阻止被情感控製的人的非理性行為(wei) 。一些人將自身的恐懼用富有攻擊性的極端方式予以發泄,這並不少見。如果我們(men) 拿海涅所寫(xie) 的《法蘭(lan) 西狀況》中1832年有關(guan) 霍亂(luan) 的報道作例子的話,就會(hui) 看到,當時巴黎的大街上,隻要有人懷疑其他人得了霍亂(luan) ,被懷疑之人就有可能被人們(men) 打死。
實際上,中國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有效的。如果我們(men) 來看一下中國科學家在當地疫情暴發之初在世界頂尖科學雜誌上發表的研究成果,就會(hui) 知道中國此前所發生的一切,我們(men) 這些國際學者都可以從(cong) 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到情況。
李雪濤:“瘴氣”一說曾風靡歐洲學術界,一直到19世紀80年代隨著顯微鏡對病原菌的發現,人們(men) 才逐漸接受科學的病菌理論。之後在歐洲發生的鼠疫為(wei) 各國科學家合作抗疫提供了契機。1897年在威尼斯召開以鼠疫防疫為(wei) 主題的國際衛生會(hui) 議,中國和日本都派代表前往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前身國聯衛生組織正是在此次抗疫的國際行動基礎上建立了。
臘碧士:盡管我們(men) 對傳(chuan) 染病的研究不斷向前推進,但有一點我們(men) 必須不斷牢記,那就是:所謂的“病原體(ti) ”也是生物。作為(wei) 人,我們(men) 不斷與(yu) 其他生物體(ti) 進行著鬥爭(zheng) ,而這些生物體(ti) 也為(wei) 了它們(men) 自身的生存與(yu) 我們(men) 做著殊死的搏鬥。我們(men) 作為(wei) 新冠病毒的宿主,它們(men) 寄生在我們(men) 身上,並且在我們(men) 身上繁衍。瘟疫便發生在原生動物、細菌和病毒之間,發生在生物和社會(hui) 的情境之中,發生在人及其生存的世界之中。如果沒有細菌的話,我們(men) 根本無法存在。
將疫情政治化同樣屬於(yu) 瘟疫
李雪濤:奧斯特哈默認為(wei) ,從(cong) 19世紀起,人類才第一次在全球範圍內(nei) 針對瘟疫展開大規模的殲滅戰。他指出,人類在這之後的抗疫鬥爭(zheng) 中取勝有兩(liang) 個(ge) 前提:一是豐(feng) 富的現代生物學和醫學知識;二是與(yu) 公共衛生政策相關(guan) 的理念。如果我們(men) 從(cong) 曆史的角度來看今天新冠肺炎傳(chuan) 播的話,還是有很多與(yu) 曆史上的瘟疫性質完全不同的地方。特別是在二戰後,航空業(ye) 的普及迅速增加了微生物病原體(ti) 的移動性。其實,瘟疫的一大特點便是流動性強,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是非常適應全球化的。新冠肺炎跟其他瘟疫一樣,也是具有軍(jun) 事化特征的人類敵人:進攻、征服、撤退。因此對於(yu) 今天的人類來講,加強全球危機管理和危機應對是至為(wei) 重要的。每一次瘟疫結束後,經曆了災難的城市乃至國家的居住條件和醫療保障都會(hui) 得到明顯改善。我們(men) 的社會(hui) 能從(cong) 這次疫情中學到什麽(me) 呢?什麽(me) 時候人類才能真正遠離瘟疫?
臘碧士:每當新的威脅來臨(lin) 之時,集體(ti) 的恐懼都會(hui) 再次引發所有已知形式的人的各種行為(wei) ,也包括錯誤的行為(wei) 。人們(men) 希望國家政治和行政部門能夠及時製定有效控製疫情的統一行動方案。但真正的理性思考往往是在疫情消退之後才開始。在急症病人麵前,醫生顯然不可能急著去修改教科書(shu) ,他必須首先去救助病患,之後才能考慮修改教科書(shu) 的事情,考慮防控疫情的計劃,考慮公共程序等。
對那些利用防疫之名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行為(wei) ,不論在哪個(ge) 社會(hui) ,都應當予以揭露。這種行為(wei) 同樣屬於(yu) 瘟疫,它發生在當代並不令我們(men) 感到驚訝,因為(wei) 疫情常常也會(hui) 被政治化。但是無論如何,在全人類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men) 還是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一威脅人類的政治瘟疫是會(hui) 得到有效控製的。
李雪濤:法國文學家加繆的著名小說《鼠疫》告訴人們(men) ,麵對荒誕的人生,重大的疫情讓人們(men) 真正去思考生命的意義(yi) 。其實疫病一直伴隨著人類的發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人們(men) ,以往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政治、經濟、軍(jun) 事的曆史並不完整,嚴(yan) 肅地看待人類的疫病史同樣是一個(ge) 重要的曆史視角。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讓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開始考慮他實存哲學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臨(lin) 界境況”:死亡、意外、罪責以及世界的不可靠性。在這些境況之中,現實世界的全部可疑性會(hui) 凸顯出來,以往被認為(wei) 是固定的東(dong) 西、不容置疑的事物、支撐每個(ge) 人的經驗以及時代的理性全都消失了,人發現自己被置於(yu) 絕對孤獨的處境之中。雅斯貝爾斯認為(wei) ,人隻有處於(yu) 臨(lin) 界境況之中,才能超越自己。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讓很多哲學家思考人類的問題。對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對人類思想變遷和文明發展帶來的改變所進行的思考,都給人以極大的啟發。
臘碧士: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yu) 人》一書(shu) 的結尾處寫(xie) 道:“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hui) 改變,但人類麵對疫病的脆弱則是不可改變的。”瘟疫與(yu) 人類的競爭(zheng) 依然存在,必將與(yu) 人類長久共存。在這裏,我想引用當代德國曆史學家馬爾特·提爾森的一句話,他說:“瘟疫是所有疾病中最具有社會(hui) 性的,它們(men) 會(hui) 與(yu) 整個(ge) 社會(hui) 相遇,激發集體(ti) 的恐懼,激化社會(hui) 的緊張關(guan) 係。”新冠肺炎疫情映襯出我們(men) 自己的真實麵目,展示了對於(yu) 我們(men) 來講什麽(me) 才是真正重要的東(dong) 西。因此,從(cong) 另外一個(ge) 角度,我們(men) 也可以說,瘟疫極大影響了人類曆史。
友情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