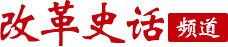魏晉玄學的法哲學價值
發稿時間:2017-11-23 10:09:54 來源:光明網 作者:沈瑋瑋
援道入儒:再續儒家正統之路徑
西漢董仲舒開創的引經決(jue) 獄,逐漸發展出了引經入律和引經注律,致西漢末年以來私家注律風靡。儒生以解經的章句之法——即離章辨句,分析古書(shu) 章節句讀的方法,來解釋律條隨之興(xing) 盛,中國傳(chuan) 統律學得以形成。因經學分為(wei) 今文經學與(yu) 古文經學兩(liang) 派,二者對律文的解釋並不相同,形成了類似於(yu) 百家爭(zheng) 鳴的律學格局。加之,東(dong) 漢以來的經學又限於(yu) 章句訓詁,西漢探究微言大義(yi) 的經學傳(chuan) 統被完全忽視,崇尚繁複的解釋一時成為(wei) 學術時尚。(【美】楊聯陞:《中國製度史》,彭剛、程剛譯,鳳凰出版傳(chuan) 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頁。)此一學術風氣導致當時的注律章句竟“十有餘(yu) 家,家數十萬(wan) 言”,使得“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wan) 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wan) 二千二百餘(yu) 言。”(《晉書(shu) ·刑法誌》)這完全是人為(wei) 地為(wei) 法律適用製造難題。同時,由經學發展來的讖緯迷信思想使儒家正統遭到懷疑,察舉(ju) 製的腐敗導致所選官員嚴(yan) 重地“名實不符”,“名實不符”的問題成為(wei) 當時學術和輿論討論的焦點。大多數人的主張不外是要求重新回到“名副其實”的正常軌道上,支持此種主張的理論便是儒家的“正名”和法家的“循名核實”。然而,當時動蕩的時局使這一理想主張無法實現,因此,大多數士人轉而尋求儒法之外的理論支撐,由此便聯想到道家的“無名”,試圖越過儒法之“名”的限製,為(wei) 承認既定的事實尋找理論依據。於(yu) 是,在東(dong) 漢中後期,研究《老子》之人可考者多達五六十家,逐漸興(xing) 起了一種言及玄遠的談論“三玄”(《周易》《老子》《莊子》)、辨析名理、品評人物的風習(xi) ,“會(hui) 通孔老”成為(wei) 一時風尚,援道入儒成為(wei) 解救儒家正統性的方法。(楊樹達:《增補老子古義(yi) 三卷附漢代老學者考》,中華書(shu) 局1935年版,第27頁。)
曹魏初便開始嚐試以“術兼名法,校練名理”(《文心雕龍·論說》)的名理之學,即以道家簡明的概念改造儒家。這一方法由清談和以清議為(wei) 選官標準發展而來,突出實用理性地品評人物。所謂清議,即以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為(wei) 依據考核名實,審察名理,為(wei) 政治和人事尋求一種形而上的根據。為(wei) 官者一旦觸犯清議,便被禁錮鄉(xiang) 裏,不許再入仕途。此後,品評人物從(cong) 道德風範轉向人物外貌,進而發展到人物的精神氣質,強調任性,縱情自然,形成魏晉玄學的核心主張。因此之故,玄學主張得意妄言,不求逐字逐句的意義(yi) ,但看重對精神實質的領會(hui) 。
總之,道家對於(yu) 儒家的意義(yi) 在於(yu) :一是重現無為(wei) 而治的政治意義(yi) ,以削弱皇權,放任門閥士族的特權;二是靠鬱鬱不得誌的士人借自然(道家)來反抗統治者的虛偽(wei) 名教(儒家)。進而,由援道入儒發展來的玄學家便大致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將名教與(yu) 自然更好地溝通起來,以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解釋體(ti) 係。西晉元康年間的向秀就主張“儒道為(wei) 一”,為(wei) 和平解決(jue) 儒道紛爭(zheng) 提供了新思路。另一類則是將名教和自然對立起來,利用自然摧毀現有的政治解釋體(ti) 係。曹魏正始年間的王弼即是代表,他使儒學擺脫了兩(liang) 漢神秘繁瑣的經訓形式,開出儒學重義(yi) 理而輕訓詁之學風,藉此得出“自然為(wei) 本,名教為(wei) 末”的結論,以道家原則統禦儒家名教。而竹林時期的阮籍、嵇康因不願與(yu) 司馬氏政權合作,從(cong) “名教本於(yu) 自然”出發,強調“貴無”和“言不盡意”而歸於(yu) 道家,旨在戳穿當時禪讓政權以儒家名教為(wei) 幌子的陰謀。“貴無”欲取代儒家理想人格,“言不盡意”則意在否定儒家經典。正如魯迅所言,竹林儒生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是偶然崇奉。(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yu) 藥及酒之關(guan) 係》,載魯迅《而已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當時,傅玄、楊泉、裴頠等人對此種亂(luan) 禮狂放之風進行了強烈反駁,“名教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論戰成為(wei) 東(dong) 周之際“禮崩樂(le) 壞”之後思想爭(zheng) 鳴的翻版。就此來看,魏晉玄學決(jue) 非如後世所想象的那麽(me) 超然和空洞,而是真實貼合了當時社會(hui) 經濟和政治文化的一套意識形態理論。(唐長孺:《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載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ong) 》,商務印書(shu) 館2010年版。)
援佛入儒:再造律學之方法論
東(dong) 漢以來繁瑣的解經之法,以及形成的章句律學,讓士人對律法之現狀和前景產(chan) 生了懷疑。佛教於(yu) 是傳(chuan) 入中國,其所倡導的簡單色相之理,促使魏晉儒生對簡約而自然的思維和行為(wei) 方式發生興(xing) 趣,玄學對簡約的崇尚正是佛教影響的結果。簡約之法需要建立在對“名實不符”的撥亂(luan) 反正之上,重建“名”之意義(yi) ,回顧本初之自然,是佛教對玄學的啟示。於(yu) 是,我們(men) 所看到的魏晉士大夫,多崇尚和迷戀清談。魏晉之際的清談多是一些與(yu) 現實無關(guan) 的清高之談,有時隻求壓倒對方,最後所得結論可能並非根本原理,故而成為(wei) 問答遊戲,類似於(yu) 兄弟利弊,肥與(yu) 瘦,茶酒論之類的論題,看似空對空,實則已是抽離的概念化思辨。而正是此種以辨名析理、注重概念、講求邏輯、建構自身理論體(ti) 係為(wei) 歸旨的玄學,其所開辟的“執一統眾(zhong) ,以簡禦繁”的方法,才使得繁雜的漢法到了魏晉之際能變得簡潔有力。(劉篤才:《論張斐的法律思想——兼及魏晉律學與(yu) 玄學的關(guan) 係》,載何勤華主編《律學考》,商務印書(shu) 館2004年版。)
這一方法被西晉律學大家張斐發揮的淋漓盡致,他利用20個(ge) 重要的法律概念開始對《泰始律》“瘦身”:“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wei) 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kui) 禮廢節謂之不敬,兩(liang) 訟相趣謂之鬥,兩(liang) 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製眾(zhong) 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yi) 之較名也。”除此之外,張斐還應用有限歸納法強調了律典總則的意義(yi) 。西晉時的另外一個(ge) 律學大家杜預,則在規則的類型化方麵使用歸納而非演繹的方法,為(wei) 精簡律典貢獻良多。他主張以“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製”(《太平禦覽》卷六百三十八)來區分律令之關(guan) 係,使晉律更加科學。總之,張杜二人利用玄學辨名析理之法,分別在概念化和類型化方麵樹立了律法的典範。這又是玄學為(wei) 魏晉律學的發展所貢獻的重要方法論。
儒釋道一體(ti) :再造律學之本體(ti) 論
魏晉玄學不是消極出世的,而是積極入世的。在餘(yu) 英時看來,魏晉士大夫,包括竹林儒生的精神有其積極的、主動的、創造的新成分,即“個(ge) 體(ti) 自覺”或“自我發現”。(餘(yu) 英時:《名教思想與(yu) 魏晉士風的演變》,載餘(yu) 英時著《士與(yu) 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頁。)“自我發現”兼有道家“放浪形骸”和佛家“人世輪回”的成分,更有儒家強調“自我實現”的實踐哲學意味,因此,其關(guan) 涉的是儒學的意義(yi) 與(yu) 前途。長期的政局動蕩,上至官吏下至百姓,皆為(wei) 命運和前途擔憂。尤其是在東(dong) 晉南渡之後,儒生開始普遍關(guan) 心儒學傳(chuan) 統延續的問題。自公元418年劉裕北伐後,南方的漢人幾乎再也沒有機會(hui) 去恢複北方失地。當政權漸被日益軟弱頹廢的上品世族把持後,作為(wei) 數量龐大的下品寒門對北伐是心有餘(yu) 而力不足,因此,隻能承認南北暫時割裂的事實,更好地兼容或同化北方,才能最大程度保持儒家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儒家衛道士的魏晉士大夫,時常在思考如何打破因南北分裂而人為(wei) 製造的文化隔閡。最後,隻有打破名教區隔,不再看重正統之爭(zheng) 和文化優(you) 越感,南下的中原儒生才能接受異族統治北方的事實。正所謂“華夏一家親(qin) ”,在他們(men) 看來,已被逐漸漢化的北方異族,以及維持北朝統治根基的依舊是中原傳(chuan) 統儒家法政文明,包括中原儒生以及西晉律法都為(wei) 北方統治者所接納,並發揚光大。在此法政格局下,南北之別逐漸被消解,南方的士人開始接受北方的異族文化。這一思想轉變達成的“南北共識”,正是魏晉人士在北伐無望的前提下,打破“誰是正統”的名教之別,接受既成事實,“任其自然”的結果罷了,因此,“自然”被賦予一種政治上默認和形成共識的內(nei) 涵。
總而言之,東(dong) 漢以來持續了近3個(ge) 世紀的玄學實際上是儒釋道“三位一體(ti) ”的作用結果。言及此,正是傳(chuan) 統經學支配儒學名教,導致儒學之“名實不符”的危機,才讓援道、佛入儒成為(wei) 可能,經由圍繞“名教與(yu) 自然”關(guan) 係的討論,讓源自於(yu) 經學的律學才可能發現繁瑣的弊端,逐步擺脫經學的束縛,回歸簡約之理,形成自身的名副其實的體(ti) 係內(nei) 容。並且,“名教與(yu) 自然”的命題本身即關(guan) 照了作為(wei) “正名”的法律之功能這一議題。“名實不符”催生了魏晉類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念,也即不拘泥於(yu) 名教之本,不需要一味受禮教約束,因為(wei) 名教的功能畢竟有限,否則不會(hui) 出現“名實不符”且無法解決(jue) 的困境。基於(yu) 名教發展而來的律法,不論如何精致細密,依然無法囊括“自然”(世間)的各種情形。於(yu) 是,魏晉士人不得不開始承認律法功能的局限性。承認名教的有限,則是承認了人類的有限,這契合了道家的“法自然”和佛家的“諸色皆空”之意。如此,律法擺脫了基於(yu) 名教發展而來的繁瑣經學之束縛,才能夠遵循自身的規律而發展。這便是玄學為(wei) 魏晉律學在揚棄漢代律學之基礎上獨立發展所提供的法哲學觀,也是魏晉再造律學的本體(ti) 論。
綜上所述,魏晉玄學在本體(ti) 論和方法論上為(wei) 律典的精簡完備和律學的獨立發展變革,提供了法哲學意義(yi) 上的啟發和指引,同時為(wei) 融通南北和異域思想,再續儒家文明傳(chuan) 統在文化意識形態上的絕對統治地位,以及再造隋唐帝國多元一統的法政哲學奠定了基礎。■
友情鏈接: